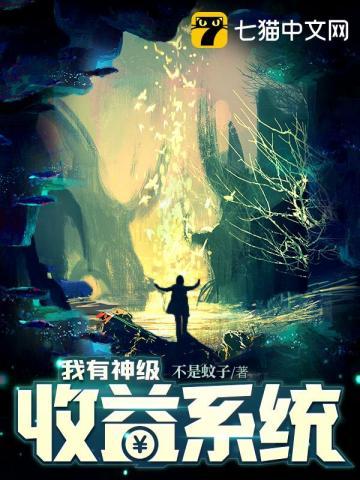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破雾航线 > 战归噩耗(第1页)
战归噩耗(第1页)
酷暑的夜晚,月光照耀下没有丝毫凉爽。
逼仄的夹角内,一个男孩抱住膝盖,坐在粗糙的编织凉席上。他认真地抿住嘴巴,双眼却空洞无神,正低头用手指一只只掐死白蛆。母亲倒在血泊中的尸体早已腐烂,冰凉的臭气渗进每一根头发丝。他浑然不觉害怕,依旧固执地呆在母亲身边。
蛆肉塞满了指甲缝,仿佛母亲的爱意填补空虚。或许将这些白蛆全部杀死,母亲就能回来。他如是想着,机械又反复地摁死它们,陷入难以自拔的偏执。
但你已经死了。我比谁都清楚。
直到男孩没力气掐死那些白蛆,而它们还在癫狂繁殖。干透的泪痕再次被淋湿。他握拳狠狠砸向凉席,悲愤嘶喊母亲为什么要丢下自己,却更痛恨自己为什么没能守在母亲身边保护她——
“把它们都杀了,我能得到什么!”他气喘吁吁,加剧了身体原本就莫名的疼痛,一时只剩含糊不清的呜咽,“我什么也得不到……”
他慢慢蜷缩自己,不再说话。
破旧的木门忽然“吱呀”响了。男孩抬头,啜泣中看见另一个半身是血的人。那人面带疲倦,像男孩一样气喘不止,似乎从哪儿长途跋涉而来。但他却在看见男孩的瞬间笑了,似乎他就是旅行的终点。
“找到你了。”
那人刚准备朝男孩伸手,想带他从图景离开,却在发现尸体后不动声色地把手收回去了。他环顾四周,大概在确认这里的位置,然后轻声询问男孩需不需要陪伴,他可以陪他在这里坐一会。
男孩点头了,很快夹坐在母亲和那人中间,不大的凉席又拥挤几分。他嗅到那人满身的杀意,但他不害怕,还隐约感受到某种宁静,来自未能识别的爱意。
“你很痛。”他对那人道。那人一愣,轻笑着说是啊,你在外面快把我掐死了。
男孩连连摇头,怕他误会似的,焦急解释自己并没有这种想法。
“我知道你没有。”
那人大概是累了,瘫软身体靠在窗台小憩。月光照亮了那张挂彩但难掩俊秀的面庞。他轻声安慰道:“是我让你失控了。不用担心,我答应带你回去……陪你坐一会吧。很久,很久没在这里见过你了。”
于是他们重回沉默,在黑暗中共享静谧与伤痛。
片刻后,男孩有所感应般扭头,看见那人脸色发紫,豆大的冷汗沁在额头上。潜意识告诉他必须马上和那人一起离开这里,否则会有危险,便开口说我们走吧。
“嗯,”那人平复一会起身,朝男孩伸手,“把手给我吧,乖狗。”
……
……
江别羽很少见若普的意识体处在童年时期。或许那个子体对他说了什么,让他受到了某种刺激。
杀掉那个恶意冒犯他的子体轻而易举,最大的困难反倒是因为失控突然攻击自己的搭档。江别羽侵入若普的图景,明明在图景外艰难躲避追杀,他却在看见若普年幼意识体的瞬间立即打消强制带离的想法。
若普并未刻意向他隐瞒过去,但讲述的口吻一向冷淡,他本以为若普和自己不同,已经从过往走出……
原来没有。
所以他选择留下,只是不想让爱人孤独陷入苦痛又扭曲的回忆。
“把它们都杀了,我能得到什么?”
从图景离开前,一直沉默不语的若普忽然开口说话了。江别羽很快回头,望见那双漆黑瞳孔中没有丝毫孩童的纯真,反倒汇聚一团迷茫挣扎的浑雾。
“把谁杀了?”江别羽问。
“随便,无论什么……”越接近清醒,记忆也逐渐混乱对冲,若普牵紧江别羽的手,低声道,“把它们都杀了,乔老师说能得到和平;和平之后,庄老师说能延续爱……但我不能理解。我能得到什么?”
他或许期待江别羽能告诉自己一个完美的答案,但江别羽咧嘴笑了,故意捉弄似的颔首。
“你能得到我。怎么样,乖狗,你要不要?”
明明是个不正经的回答,却令男孩心热脸红,烫得耳朵都要掉了。
“我要,”他移开视线,似乎想起某个为之拼命的信念,呓语般坚定道,“你也不知道……但江别羽,我会让你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