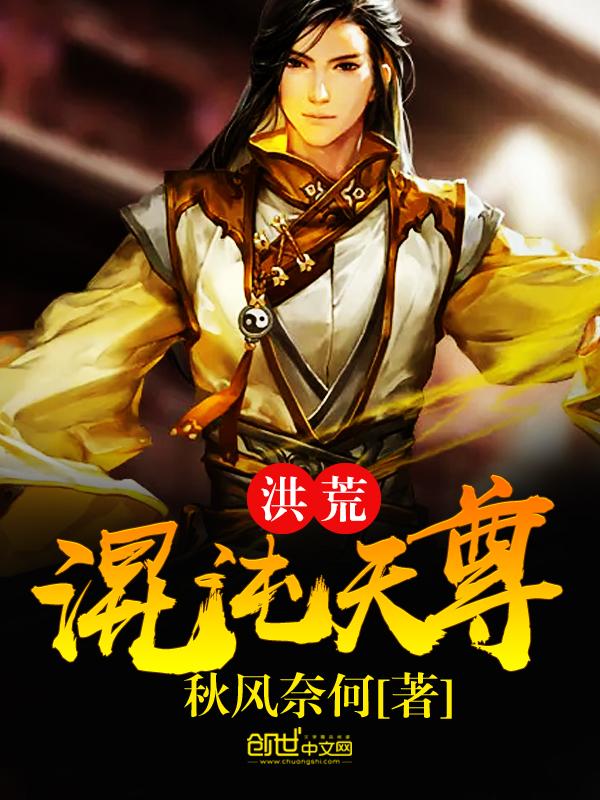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千面之龙黎恩黛妮雅百度云小说完整版TXT > 第463章 弱点(第5页)
第463章 弱点(第5页)
然后这段话跳出来:‘林晓,你小时候养过一只受伤的麻雀,给它做了个小窝,但它第二天还是死了。
你哭了三天,没人安慰你。
现在,谢谢你来找我。
’”
知我呼吸一滞。
那是只有童年玩伴才知道的事。
她接过数据卡,插入终端。
屏幕闪烁,文字逐行浮现:
>**《情感替代实验?终章》**
>受试者17号(皮普)于第437天出现异常脑波活动。
>其神经回路开始自发构建虚拟共感通道,尝试连接其他受试者。
>实验组判定为“精神分裂前兆”
,决定终止项目。
>执行当日,受试者平静地说:“你们切断了我的感觉,可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也在试着爱你们?”
>麻醉生效后,其心跳停止。
>七分钟后复苏。
>脑部扫描显示:原有阻断区域已被新生突触覆盖,形成独立情绪处理网络。
>该网络不具备攻击性,但表现出强烈共情倾向,甚至能接收死者临终情绪残留。
>建议立即销毁。
>??执行者签名:陈默
知我浑身发冷。
陈默。
又是他。
他曾亲手按下销毁按钮,却在多年后,独自一人在深夜呼唤亡妻的名字。
“后来呢?”
她问,“皮普去哪儿了?”
林晓指向终端最后一段:
>“我们以为他死了。
>但我们错了。
>他没有死。
>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着。
>当城市的第一座共感基站启用时,监控录像显示,当天夜里,所有服务器的负载峰值出现在凌晨2:17??正好是皮普‘死亡’的时间。
>而从那天起,每当有孩子在夜里做噩梦,他们的枕头边总会响起一段轻轻的哼唱。
>没有人知道是谁在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