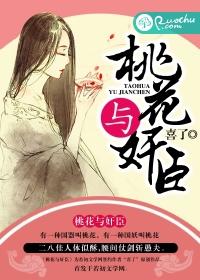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天龙人,同龙不同命 > 君子小人真假意无苛(第2页)
君子小人真假意无苛(第2页)
又是几日,林兮日日晨起去与张鹏练剑,他将那本《白陵纪要》带上,练剑时亦是用脱下的外衫将书册包裹得严实。不过两日,张天官便带着妻子姜成绮来与张鹏请安问早。
他二人围坐在石桌边,林兮挥剑片隙瞧见,姜成绮眼珠子时刻不离放在石墩上的外衫,只是张天官一直在旁,她并未有什么动静。直至林兮练完剑,张天官夫妇都未离去。林兮穿套外衫时,特意将那本书在姜成绮前闪了一眼,随后迅速揣入怀里。
再过一日,张天官与姜成绮带着两提食盒来看他练剑。林兮心觉,姜成绮该是要有所行动,只继续按着张司宇的意思,引狼入室,将计就计。
果然,在茶歇时,姜成绮不慎将满满一碗茶打翻向林兮。
“林公子,都是我粗心。”姜成绮说道,“天气寒凉,公子若不嫌弃,可先换了外子衣袍来穿。”
林兮回道,“多谢少夫人。”
张鹏也关心道,“天官,快带林兮去更衣,别冻着他了。”
张天官应声道,“走,林兮,随我去。”
待林兮与张天官再回到张鹏处时,见只姜成绮一人在石桌旁。
张天官细询才知,姜成绮听公爹聊起墨白城内有柄绿绮剑,她听这把剑是与自己同名,好奇想看看,张鹏便到剑室取剑去了。
不会儿功夫,张鹏便带回一柄周身通绿如碧的剑来了。见着姜成绮对绿绮剑又赞又叹的模样,林兮心想,如不是司宇事先洞明,真是险些被她骗了。
林兮练过剑后,便揣书告退,回到流云居后,打开一看,这本虽和事先张司宇交予自己的那本《白陵纪要》是同版刊印,但记有白陵龙脉之事的那页,并无张司宇事先做旧的痕迹,显然是被调包了。
张司宇满意淡笑,对林兮说道,“做人做事,一定要禁住诱惑,三思而行,任何好巧,都可能是圈套。”
“司宇,你确定姜成绮会以为你是去寻龙脉吗?”
张司宇默默阖上眼皮,“陈雅安见微知著,这点小动作瞒不过他的。所以,但凡我有一丁点风吹草动,他都将大费周折。”
林兮问道,“那还敢让他知道,万一他们真的寻到龙脉了呢?”
张司宇说道,“伯父说过,龙脉是可见不可得之物。”
林兮晃了晃头,“跟他们兜这么大一圈,到底要做什么?”
张司宇提笔写下一串姓名,敲着宣白纸张问道,“猜猜这几人是谁?”
林兮望去,沈炼,肖垂,姚重九,姚上元,岳刚,“我若猜的不错,他们便是白陵的五军统将了。”
“不错,这些人中,即便是资历最浅的岳刚,从军也快二十年了。”
林兮扭了扭眉,难怪张司宇如此眼重姚远舟的兵权,又分毫奈他不得,原是姚远舟手下的人,皆是老将,“姚都督才逾五十,怕是再过十年,这班人马也是牢如铁桶。”
张司宇点着肖垂名字,“肖将军今年六十有五,再有三五年,也该解甲了。姚远舟这几年一直在考虑该由谁来接掌北军。”
林兮无奈笑了笑,“姚都督将有天作这位乘龙快婿,想来心里快有答案了。”
张司宇看着林兮对自己有声应声,有命从命的模样,叹道,“这位子本来是属于你的,如今,也只能给你另谋出路了。”
晨曦初破,不等第一缕阳光探入流云居,张司宇便持枪立身屋外练功。
伴着银枪划过空气的呼呼声,林兮也渐渐醒来。自到墨白城以来,他便一直与张司宇同住流云居,他睡床,张司宇卧榻,林兮盖棉被,张司宇盖单被。
从张鹏处练剑回来,张司宇带他去了桃李苑,二人还未进门,就听屋内传来朗朗读声。
暖阁内,矮松木架间,皆是香炉棋枰类的精致玩件儿,一儒衫老者坐在一张花梨小几旁捧书默诵,旁边几上摆着细颈青窑瓷瓶,里面插放一束时兰。
张司宇恭身拜去,“孙儿见过外祖。”
林兮闻声,双手作礼,面着顾友庭深鞠一躬,说道,“小辈林兮,见过顾阁老。”
顾友庭起身,领二人进了内室,三人围着一张金漆方桌坐下,桌上摆着数盘鲜果蜜饯。
张司宇再度介绍道,“外祖,林兮便是我与您提过的,作出《哀乐论》的那位小兄弟。”
顾友庭,仔细端了端林兮面态,见这小伙墨发高扎,额前碎发风动,不住大赞道,“前几日司宇还带了你的诗词来,万里功名,白马银鞍飒沓河汉。当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啊。”
林兮谦逊地半点起额头,“阁老谬赞了。”
张司宇开口道,“林兮,外祖曾是东海城竹贤阁阁老。如今瑶光太学学正祈大人,正是他门生,待你寻访过白陵地貌,我就将你安排进太学,一面著书,一面协助祈大人在民间开设教坛,争取早日为寒门学子敞开仕途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