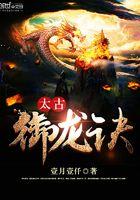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鱼玄机传 > 心意(第1页)
心意(第1页)
天启十一年,寒食节刚过。
天色未明,长安城笼罩在一片薄雾中。一辆青篷马车悄无声息地停在温府后门。
玄机在青杏的搀扶下踏上车,她回头望去,温府的轮廓在晨曦中沉默无语。这里装着她半生的悲欢,而此刻,她心中只剩一片卸下重担的平静。青杏紧随其后,抱着一个装着细软的包袱,也利落地登上了马车,安静地在玄机身侧坐下。
温庭筠最后与儿子交代了几句,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利落地登上马。
“都收拾妥当了?”他问,声音在寂静的街巷中格外清晰。
玄机颔首。
温珏低声道:“父亲,师妹,一路保重。”
马车缓缓启动,他们像一滴水,悄然汇入即将苏醒的都市,然后无声无息地蒸发、消失。当第一缕晨光终于照亮承天门时,他们的马车已驶出明德门,将那座辉煌而沉重的长安城,永远地留在了身后。
马车颠簸在南下的官道上,扬起细细的烟尘。
温庭筠骑在马上,与马车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透过车帘,依稀可以看见车厢内的情形。
多数时候,玄机是靠在车壁上假寐。她身侧的青杏也昏昏欲睡,脑袋一点一点的。每一次颠簸,玄机纤长的眼睫就会轻轻颤动,在苍白的面容上投下脆弱的阴影。她那微蹙的眉头,像一根细针,刺在温庭筠心上。
舟车劳顿,水路陆路交替,辗转整整一月有余。
这一日,马车终于驶入岭南道治所所在的州城。他们并未在喧嚣的城中久留,温庭筠早已托旧友在此地远郊,寻了一处依山傍水的小院。
院落白墙黛瓦,格局简朴,推窗可见苍翠山色,确是一处避世幽居的好所在。
岭南的时日,便在一种刻意的平静中缓缓流淌。转眼,他们在此地已住了一月有余。
最初的安顿忙乱过后,生活仿佛陷入了一种停滞的胶着。温庭筠似乎又退回到了“先生”的身份里,每日里或整理旧稿,或出门探访岭南风物,与玄机相处时,言语举止皆恪守着分寸。
他为她寻来当地志书,与她探讨岭南诗文与中原的异同,关心她的饮食起居,无微不至,却始终隔着一层看不见的、名为“礼法”的薄纱。
玄机身上的疲惫渐渐被岭南温润的水土抚平,脸颊恢复了少许血色,但心底那份空茫,却并未因环境的改变而消散,反而在日复一日的“相敬如宾”中,沉淀得愈发沉重。
她有时会独自坐在院中那株高大的榕树下,看着虬结的树根在风中微微摆动,一坐便是半日。
她不知道温庭筠怎么想,只是开始怀疑,自己抛下一切,随他远遁万里,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只是为了换一个地方,继续那令人窒息的“师徒”名分?
这日傍晚,残阳如血,将小院染上一层暖橘色的光晕。温庭筠与玄机于堂中石桌前对坐用膳,席间只有碗筷轻微的碰撞声和远处隐约的虫鸣。膳毕,僮仆撤下残羹。温庭筠沉吟良久,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方抬眼看向玄机,目光温和,却带着一种刻意维持的、属于师长的疏淡。
“幼薇,”他开口,声音平稳,听不出太多情绪,“你我既已离了长安,前尘往事,皆如云烟。此地虽僻远,却也清净,正适合潜心学问。”
他顿了顿,避开玄机渐渐凝住的目光,继续:“在此处,我仍以弟子礼待你。一切起居用度,自有僮仆打理,你无需费心。学问之道,永无止境,我们……”
他的话未曾说完。
玄机猛地抬起头,脸上那一个月来勉强维持的平静,瞬间被一种难以置信的、尖锐的刺痛所取代。她看着温庭筠,看着他那双试图维持平静却难掩复杂情绪的眼睛,看着他口中吐出的“弟子礼”这些字眼,只觉得一股冰寒彻骨的气息从脚底直窜头顶,将她整个人都冻僵了。
“弟子礼?”她轻轻重复着这三个字。
那声音里的寒意,让温庭筠的心猛地一缩。
一路同行,万里相随,离经叛道,抛却长安所有。她以为,彼此心中早已有了超越世俗的默契。她以为,他带她来此,是终于肯直面二人之间那纠缠多年、无法言喻的情感牵绊。她以为,在这远离是非的岭南,他们可以挣脱一切枷锁,换一种身份,重新开始。
却原来,竟还是“师徒”!竟还是“弟子”!
那他为何要带她走?是怜悯?是责任?还是他温飞卿清名之下,那点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可怜的“道义”?她鱼玄机在他心中,永远只是一个需要他教导、需要安置的“弟子”。
巨大的失望与屈辱,如同汹涌的潮水,瞬间冲垮了她连日来强撑的平静。她想起离京前湘儿转述的师娘遗言时,自己的感动与释然。想起他说可否和他一起去岭南时,她毫不犹豫的回复。
此刻只觉得像个天大的笑话!所有的期盼,所有的孤注一掷,原来都是她一个人的痴心妄想!
她霍然起身,椅子在青石板上划出刺耳的声响。
“先生……”她看着他,忽然低低地笑了起来,那笑声凄楚而悲凉,带着浓浓的自嘲,“好一个‘弟子礼’!好一个‘潜心学问’!原来在先生心中,我鱼玄机万里相随,竟还是为了这虚无的学问!”
她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积压了太久太久的委屈与愤懑:“既然如此,先生当初何必带我离开长安?何必让我生出……生出那些不该有的妄念?”
话音未落,泪水已决堤而出。
“幼微。”
“不要叫我!”玄机猛地后退,转身欲要夺门而出。
温庭筠看着她眼中熄灭的光,那股长期压抑的、混合着恐惧与深沉爱欲的情感,如同积压已久的火山,轰然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