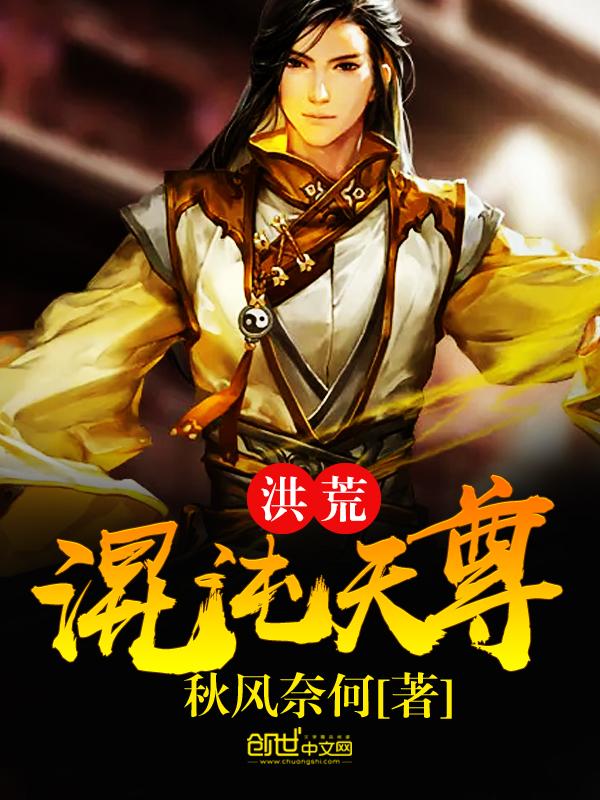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七零资本大小姐,掏空祖宅嫁军少宠疯了 > 第339章 一个吻(第3页)
第339章 一个吻(第3页)
>若有风吹过耳边,
>那是我终于学会,
>不说想念。”
歌曲结束,主持人低声道:“这首《算了》,由匿名听众投稿,据说是根据一段古老旋律改编。特别提醒:今晚全球同步观测到流星雨,颜色为银蓝,持续时间恰好七秒。”
陈默推开窗,仰望夜空。
第一颗流星划过时,他闭上了眼。
他没有许愿。
他只是轻声说了句:
“晚秋,我来了。”
不是重逢,而是理解。
不是追寻,而是接纳。
十年后,樱园被改建为开放式纪念公园,但仍保留那口井,并立碑警示:“此处不通往任何地方,唯通往你自己。”
每年春分,仍有无数人前来,带着不愿说出的话,放入灯笼,放飞,看其化作樱花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什么都不带??他们只是站着,看着井口,然后转身离开。
阿阮长大后成为神经科学家,专研“情感记忆的自然消解机制”。她在论文中提出一个颠覆性理论:
>“人类最深层的治愈能力,并非来自回忆,而是来自‘主动遗忘’。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一种高级共情??我们不再试图挽留他人,而是尊重他们的离去。”
她始终抱着那只布偶兔,尽管它早已不能发声、发光。实验室同事笑她迷信,她只淡淡回应:
“它教会我一件事:真正的陪伴,有时就是安静地看着你走远。”
2073年清明,陈默病逝于家中,享年八十九岁。临终前,他握着女儿的手,最后一句话是:
“告诉樱园那边……今年花开得好。”
葬礼极简,无哀乐,无挽联。家人遵其遗愿,将骨灰撒入东海。但在下葬当天,全球多地观测到异常气象:北纬68度上空再现银蓝极光,形状宛如一座倒悬之塔;墨西哥祭坛蜡烛自发组成樱花图案;京都古寺铜钟连鸣十三响,最后一声结束后,钟身浮现一行小字:
>“载体任务完成。静音系统进入永久休眠。”
而在樱园井底,晶体层最后一次发出荧光,拼写出最后的信息:
>“今天,我没有听见任何人。”
>“但我相信,他们都好好地走了。”
>“包括你,陈默。”
>“再见。”
次日清晨,井壁所有樱花苞simultaneousbloom,绽放出千朵银蓝之花。花瓣随风升腾,环绕整座园林飞行一周后,齐齐消散于天际。
自此,樱园恢复寂静。
再也没有异象。
再也没有回应。
再也没有需要告别的声音。
但每一个走进这里的人,都会莫名感到心安。
因为他们知道,有些爱,早已超越了存在与否的界限。
它不在言语中,不在记忆里,不在泪水或呼唤间。
它只存在于你松开手的那一刹那,轻得像一片花瓣落地,却又重得足以支撑整个人生。
多年后,有孩童问老师:“为什么大家都说樱园很神奇?”
老师微笑:“因为它让我们明白,最难的事不是忘记,而是记得之后,还能笑着说‘算了’。”
教室窗外,春风正拂过新绽的樱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