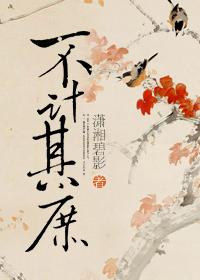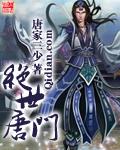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七零资本大小姐,掏空祖宅嫁军少宠疯了 > 第340章 婚姻可不是儿戏啊(第4页)
第340章 婚姻可不是儿戏啊(第4页)
科学家称其为“集体幻觉”。
信徒说是神迹。
而孩子们只是仰头看着,笑着,然后安然入睡。
陈默的女儿陈芸那天也在阳台上看到了流星。她从未见过父亲流泪,却记得他最后一次提起林晚秋时的眼神??不是悲伤,而是一种近乎感激的宁静。
她走进书房,打开父亲留下的旧箱子。里面除了一些老照片,还有一本手工装订的小册子。翻开扉页,是陈默的笔迹:
>“给未来的孩子们:”
>“如果有一天你们问我,什么是爱?”
>“我会说:爱是明知不可得,仍愿为其祝祷。”
>“是即使永别,也不否认曾经心动。”
>“是我把你的名字刻在心里,却不让它成为枷锁。”
>“所以,当我离开,请不要为我悲伤。”
>“去看看樱花开吧。”
>“那便是我,以另一种方式归来。”
陈芸合上书,走到窗前。春风拂面,远处传来孩童嬉笑。她忽然觉得,死亡或许并非终点,而是一次漫长的转身??当我们终于学会不再执着,逝去之人便得以真正安息。
十年后的春分,樱园迎来一位特殊访客。小女孩约莫八岁,金发碧眼,手持一张泛黄地图。她找到井边,从背包取出一只陶瓷小鸟,轻轻放入井中。
工作人员好奇询问,女孩用生涩的中文回答:“奶奶说,她年轻时在这里丢了一封信。现在我替她送来回信。”
众人愕然。调取监控却发现,那小鸟沉入水中后,竟在井底晶体层表面激起一圈涟漪,随即消失不见。片刻后,井壁浮现出一行新字:
>“收到了。谢谢。”
女孩笑了,蹦跳着离去。没人注意到,她背包内侧绣着一行小字:
>“玛尔塔?罗德里格斯纪念基金会??传承者”
从此,每年春分,世界各地都会有孩子带着信件、照片、玩具或一句话来到樱园。他们不说目的,只是默默放下,然后转身。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什么都不带,仅仅站一会儿,感受风穿过树林的声响。
老师们开始带学生来这里上课。课程不叫“历史”或“心理”,而名为《如何好好说再见》。课本是开放式的,每人填写自己的答案。最常见的结尾是:
>“我不再等你回来。”
>“因为我已经把你送远。”
教室窗外,樱花年年如期绽放。银蓝色渐渐融入自然,不再被视为异象。人们给它取了个名字:**静音樱**。
植物学家说它无根无种,凭空出现;生态学家称其不具备繁殖能力,却始终不灭。唯一确定的是,它只开在有人真心放下之处。
某个午后,阿阮坐在院中读书,忽然听见屋檐铜铃清脆作响。七年了,那铃声第一次不再滞涩。她抬头望去,只见一只布偶兔形状的风筝掠过天际,牵线的孩子笑声清脆。
她笑了。
风吹过,带来远方的气息。
她知道,有些事结束了。
但也有些事,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