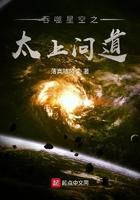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贺尚书她绝对有病 > 第258章(第1页)
第258章(第1页)
贺重玉从袖口掏出那副加盖了玺印的圣旨,回道:“不处置。”顿了顿,她继续说,“只不过,之后他做刺史,你做司马。”
一双眼睛还没从那副明黄的卷轴上抽开,傅长青就听到了如降甘霖的一番话,肩膀一松,“应该的应该的,小臣治下不严,还要谢圣上仁慈,贺尚书您请。”他殷勤地为贺重玉推开门。
狐貍不像狐貍,老虎自然也不像老虎,正对贺重玉而坐的人,长着一张普通到扔进人堆里都找不出来的脸。
“我想不通一件事,望李将军为我解答。”
“何事?”
“既无心谋逆,为何行此悖乱?既已决意归附,为何指名让我前来招安?”贺重玉是真的困惑,而且这个李怀安到底是何方神圣,他就跟天上掉下来似的,从前不露山露水,结果冷不丁一出现就掀起惊涛骇浪。
“你现在倒是比小时候爱说话。”他轻笑。
“什么?”贺重玉微微一愣,见面前推来一杯茶。
李怀安放下茶壶,手里转着空茶杯,眼中有股久别重逢的亲切,“我不知道你长大是这样的,比我想的要……英武。”他笑眯眯地开口,“不记得了?春日宴,城隍庙。”
“你是……老三!”时隔多年,贺重玉终于见到了雨师面具下的真人,不禁失笑,“你们真是所图甚远啊,少说十数年的谋划一朝成为泡影,你不后悔?”
“后悔啊,怎么不后悔。”李怀安古怪地笑着,“所以,你得劝我回头是岸,你若言之有理,我便缴械投降,你若不能说服我,那么灵州可就成了你丧命之处!贺尚书,我知你武艺高绝,可你能抵挡得过漫天箭雨么?灵州势微,不能与朝廷大军相抗,但留下你的性命可是绰绰有余啊。”
“其实最主要的缘由,你自己方才不也说了,不是么?灵州势微,不能匹敌朝廷,依势称臣才是明智之举。与其到时血流成河,生灵涂炭,依旧落败而死,不如退而俯首,共举天下太平。”
“是啊,若是普通的反贼,听闻贺尚书一席话,大概已经喜不自胜,乐得归顺了罢?”李怀安声音渐冷,“可若我说,我与朝廷有不共戴天之仇呢?”
“因为太上皇?”贺重玉习以为常地问道,“是家族覆灭?血亲惨死?还是父母含冤,抱屈而终?”
“你知道?”有一瞬间,李怀安竟以为她已经知晓一切。
“看来真是太上皇啊!”普天之下到底有多少他的仇家?这人的罪过大概跟他的功绩一样深重。贺重玉敲着桌板,似乎陷入了回忆,“因为我也是一样。”
“那你怎么敢来劝我与朝廷罢手言和?”李怀安讥诮地笑,“扪心自问,贺尚书就没有半分恨意?”
“恨么,自然是有的,不过一码归一码,我还不想因一家之仇怨而牵连万千生灵。”她没有影射对方的意思,完全是出自真心之言,这是宁州教给她的道理,现在她将其和盘托出。
“如李将军所为,在天下大乱时领兵护卫百姓,本是正义之举,有功。而如今天下将定,你只靠灵州无法和朝廷大军相抗,若一意孤行,便是徒造伤亡,这是有过。”
“功过不在我口中,而在百姓心中。我进入灵州,所见皆是和乐,所闻俱为欢欣,百姓一言一语皆是对刺史的爱戴,对将军的信奉,这便是二位治理灵州的功绩。我也相信,若你执意揭竿而起,灵州百姓愿意为你赴死。可你愿意看到原本和谐安乐的灵州死伤惨重,原本团圆美满的家庭家破人亡么?”
贺重玉接着说,“李将军,你有爱民之心,却并无夺取天下的野心,不可执意勉强。以将军的才能,为何不堂堂正正地做个有功于社稷的重臣呢?我此行便是带来了陛下的圣诏,若你愿意,灵州仍然由你执掌,今后,你便是灵州刺史。”
“那老傅得知,岂不是要哭一缸眼泪?”李怀安只是笑了笑,似乎考虑良久,才叹了一口气,“你帮我解决了一个疑难,我该谢你,自从家人故去,已经很久没有人能像这样为我出个主意了。”
他像变戏法一样从桌案底下摸出一个酒壶,“今日有喜,当庆!庆灵州永享和乐,庆你我二人久别重逢!喝酒!”他挑眉道,“贺尚书该不会害怕我在酒里下毒罢?”
“愿,天下太平!”贺重玉一饮而尽。
“好!爽快!”他大概是酒性大发,对着壶口将酒液咕咕倒进嘴里,一抹嘴巴,哈哈大笑。
“我原本自矜于才干,得知贺尚书才知井外方阔,某甘拜下风!”
“哪里,身有托举之人,比不得将军自强不息。”
李怀安也毫不客气地接下了这句夸赞,“那是!”他眉飞色舞地讲起年轻时的过往,“当年啊,我还是亭山下的猎户,县令横征暴敛,逼得不少良家子落草为寇……”
从官家子到乡野村夫,而后成为一州之地的实际执掌者,贺重玉更加惊叹他的才能胆识,坦言道,“如果早一步遇见你,我大概会选择助你一臂之力。”后面紧接着极快极低地嘟囔了一句——太上皇?狗都不搭理!
李怀安听见了最后那句话,拍着桌案笑得前仰后合,突然脸色一白,下意识地张手捂住了嘴,可殷红的血仍从他指缝里漏出来,滴滴答答落到地上。
“怎么回事!”贺重玉惊得站起,她抬手拎起酒壶,里面的酒已经被李怀安喝得一滴不剩,只剩壶底一层薄薄的暗光。
“你猜错啦,酒确实有毒……”李怀安虚弱地笑着,眼中有一丝得意,“只不过,毒在杯底。”他还有力气撇嘴,“说什么见血封喉的毒药,也没那么神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