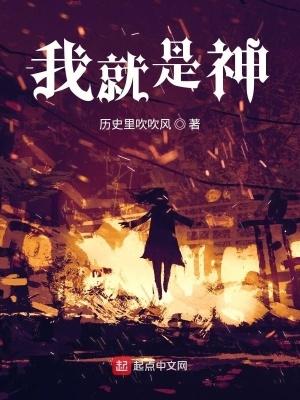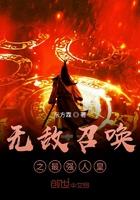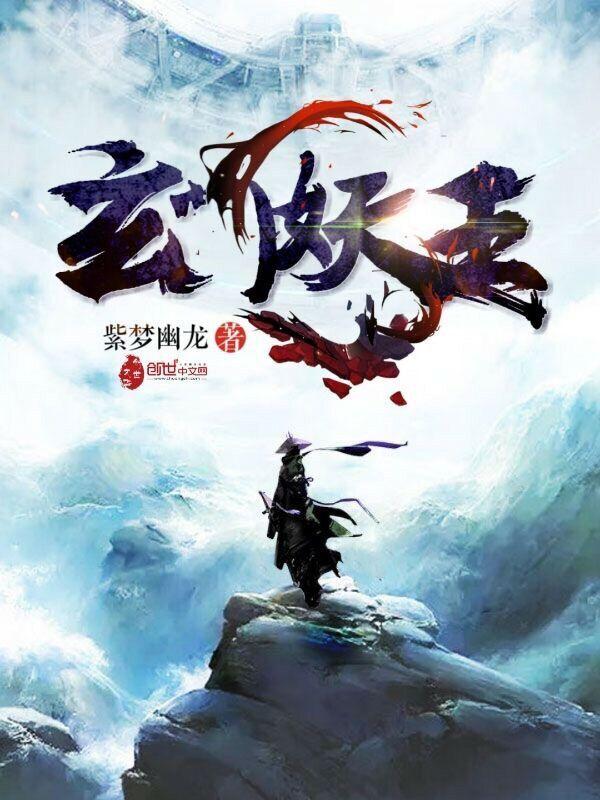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华娱,不放纵能叫影帝吗? > 第637章 纽约不夜城(第1页)
第637章 纽约不夜城(第1页)
“叮咚、叮咚。”
清脆的门铃急促响起。
过去好一会,房门才咔嚓打开。
“李!”
伊曼纽尔就要带着哈哈大笑向里面送上拥抱,可下一刻就惊得急忙刹停步伐:“厚里谢特,你们这些演员都是。。。
雪线在远处如刀锋般切开天际,阿勒泰的冬天来得比往年早。风从西伯利亚翻山越岭而来,卷着细碎的冰晶,在车窗上划出蛛网般的裂痕。时宁把暖气调到最大,可脚底仍像踩在冻铁上。赵小芸裹着两条毛毯,鼻尖通红,声音沙哑:“你说的那个老猎人……真能找到吗?这种地方,连牧民都搬走了。”
“马校长不会骗我们。”时宁盯着导航屏幕上那个微弱的红点,“他说老猎人每年冬至都会去‘熊眼泉’祭拜,就在乌尔禾林场深处。只要我们在那之前赶到,就有机会见他一面。”
“可我们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赵小芸咳嗽两声,“总不能见了面喊‘喂,疯老头’吧?”
时宁没笑。她翻开日记本,指尖抚过那页写着“看不见的熊”的纸条,轻声道:“他叫巴图尔,哈萨克语是‘英雄’的意思。但他自己说,他不是英雄,只是个还听得见山说话的人。”
车子在雪原上艰难前行,轮胎碾过结冰的河床,发出令人心悸的脆响。沿途偶有倒伏的电线杆,挂着破旧的警示牌,字迹被风沙磨平,只剩下一个模糊的“禁”字。越往北走,信号越弱,手机早已变成一块冰冷的砖头。她们靠一张手绘地图和指南针前进,每过一小时就在雪地插一根彩色布条作标记。
第二夜,暴风雪突至。能见度骤降,车灯照出去不过十米便被雪幕吞噬。她们被迫停在一处废弃的护林站,屋顶塌了一半,墙角堆着发霉的棉被和锈蚀的猎枪。赵小芸生火取暖,烟从破瓦缝里钻出去,像一条垂死的蛇。
“你说……苏日娜的事现在怎么样了?”她蜷在火堆旁,声音低得几乎被风声吞没。
时宁正用酒精擦拭相机镜头,闻言顿了顿:“老高的消息说,境外媒体已经开始跟进,但国内平台全删了。有几家小报想转载,第二天主编就被‘谈话’了。”
“所以……我们拍的,真的有用吗?”赵小芸抬头看她,眼里有疲惫,也有怀疑。
“有用。”时宁放下镜头,直视她的眼睛,“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追我们吗?不是因为我们拍得多好,而是因为我们让沉默有了形状。苏日娜跪着舀水的样子,韩素梅抱着孙子骨灰盒的眼神??这些画面一旦存在,就再也抹不掉。哪怕被封、被删、被说成造假,可总会有人记得。而记得,就是反抗的开始。”
赵小芸沉默良久,忽然笑了:“你说得对。要不然,他们也不会派陈默出手。”
“陈默……”时宁喃喃念出这个名字,像是咀嚼一块苦药。她从背包里取出那枚微型存储卡,放在火光下看了看,又收回贴身口袋。“他签了‘静音行动’,可他不知道,静音从来堵不住真相。就像沙漠里的井,哪怕被填了九十九次,只要有人再挖一次,水还是会冒出来。”
凌晨三点,风势稍缓。她们趁机出发,沿着一条几乎被雪掩埋的小径深入林区。天亮时,终于抵达地图标注的“熊眼泉”。那里是一处环形山谷,中央有一汪不冻的泉水,冒着淡淡白雾,像大地睁着一只永不闭合的眼睛。泉边立着几根木桩,挂着褪色的经幡,随风轻轻摆动。
“有人来过。”赵小芸指着雪地上的一串脚印,深浅不一,延伸进密林深处。
她们顺着脚印走了近两公里,终于在一棵巨大的冷杉后发现一间木屋。屋顶覆着厚厚积雪,烟囱冒着青烟,门口挂着一张晒干的狼皮,风一吹,獠牙微微颤动。
时宁敲了三下门。
许久,门开了一条缝。一个满脸胡须、眼神锐利的老人站在里面,手里握着一把猎刀,刀刃上还沾着未干的血迹。
“你们是谁?”他用哈萨克语问。
时宁用生涩的发音回答:“我们是从南边来的。想找巴图尔。”
老人眯起眼,上下打量她们,突然冷笑:“南边?那边早就没人说实话了。你们是公安?记者?还是……公司的人?”
“我们是拍片子的。”赵小芸掏出相机,“记录那些快要消失的东西。”
老人盯着相机看了很久,忽然伸手夺过,打开回放。画面里闪过苏日娜守井的身影、青海湖干涸的湖床、藏族孩子空洞的眼神……他的手指微微发抖。
“你拍这些……不怕死?”他低声问。
“怕。”时宁直视他,“但我们更怕闭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