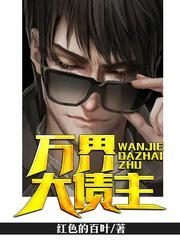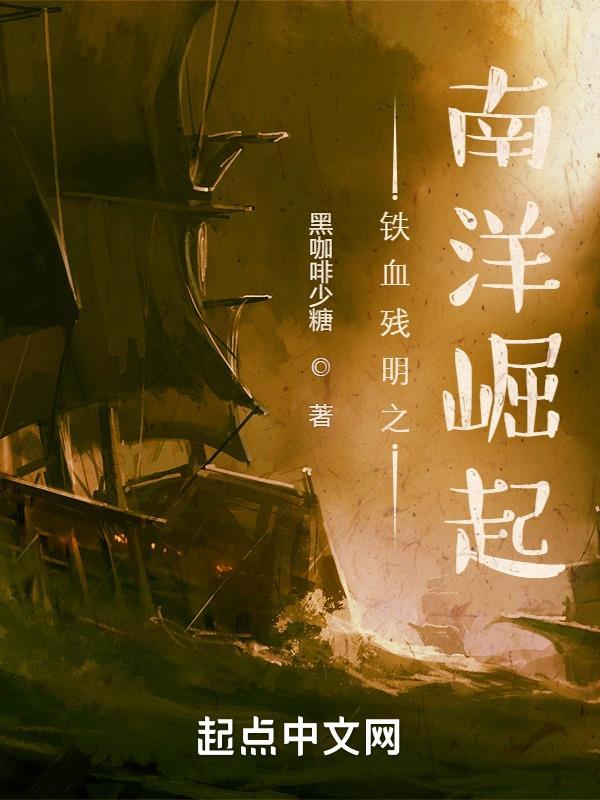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触碰蔷薇 > 第692章 为了理想而奋斗(第2页)
第692章 为了理想而奋斗(第2页)
>**“当一颗心被看见,它就开始生长;当一群心彼此映照,荒原便成了花园。”**
深夜,暴雨突至。
雷声滚过山巅,雨点如鼓点般砸在屋顶杉木板上。李灵惊醒时,听见走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她披衣出门,只见小宇正艰难地撑着拐杖往监控室赶,脸色苍白却坚定。
“温室报警了,”他说,“排水系统可能堵塞,幼苗泡水超过两小时就会烂根。”
她立刻转身取来雨衣和手电筒。两人冒雨奔向温室,途中遇到林小满带着几名村民已先一步抵达。玻璃屋内积水已没过脚踝,数十株珍贵种苗摇曳在浑浊水中,叶片微微发黄。
“水泵坏了!”一名年轻技工大喊,“备用电源也失灵!”
“打开南侧通风窗!”李灵迅速指挥,“先把高架床抬起来,优先抢救母本株!”
众人分工协作,有人搬梯子,有人扛木板垫高花架,有人用脸盆手动排水。小宇坐在轮椅上,手持对讲机协调各区域进度,声音沉稳清晰,仿佛这场风雨不过是日常训练的一部分。
两个小时后,积水退去,电力恢复。当最后一盏补光灯重新亮起,映照出满室翠绿时,所有人瘫坐在泥地上,笑声混着喘息在湿漉漉的空气中回荡。
李灵靠在墙边,浑身湿透,发梢滴水。小宇缓缓滑下轮椅,跪坐在她身旁,从怀里掏出一块干布,轻轻擦去她脸颊上的泥点。
“你知道吗?”他低声道,“刚才那一瞬间,我突然不怕雨了。”
她抬头看他:“以前不是最讨厌下雨?说雨水会毁掉初开花苞。”
“但现在我知道,”他凝视着重新挺立的一株“触脉蔷薇”幼苗,“有些花,正是被暴雨唤醒的。”
三天后,天气放晴。县电视台前来拍摄专题纪录片。镜头前,李灵带着学员们进行“沉默倾听”训练??每人蒙眼静坐十分钟,仅凭呼吸、心跳、环境音感知他人存在。
一位曾因车祸截肢的中年男子,在摘下眼罩后泪流满面:“我三十年没听见过自己的心跳……原来它一直都在跳,只是我一直捂着耳朵。”
节目组采访小宇时问他:“你觉得这个项目最大的奇迹是什么?”
他沉默片刻,望向远处正在教孩子们辨认草药的李灵,说:
“不是有人站起来了,而是那些原本不敢倒下的人,终于敢躺在别人怀里哭一场。”
采访结束当晚,村里放了一场露天电影。投影幕布挂在实训基地外墙,播放的是村民们亲手剪辑的《编年史》影像集。从第一年破败的村卫生所,到如今连片青瓦白墙的新建筑群;从王婆婆卧床不起的身影,到她今日拄拐参加插秧节的模样;从李灵孤身一人背着药箱穿行山林,到现在三十双脚步并肩走在田埂上……
影片最后定格在日内瓦演讲的画面。台上的李灵说:“真正的疗愈,是让人终于敢说出‘我很痛’。”
全场寂静。随即,掌声如春雷般响起。
散场时,李灵发现小宇不见了。她寻至山坡上的木牌处,见他独自伫立风中,手中握着一支录音笔。
“在录什么?”她走近问。
“我在收集夜晚的声音。”他按下播放键??
先是风掠过蔷薇枝叶的沙响,接着是远处溪流潺潺,再后来,隐隐传来老人哼唱的山歌、孩子梦呓般的呢喃、护工轻拍失眠者背脊的节奏……最后,是一段极轻的啜泣声。
“这是谁?”她轻声问。
“上周完成生命走访的学员小陈的母亲。”他说,“她儿子陪她整理亡夫遗物那天,她第一次打开了那个锁了二十年的樟木箱。我没进去,就在门外守着。等她出来时,眼里有泪,但嘴角是笑的。”
他关掉录音,抬头看她:“我想建一个‘声音档案馆’。不记录成就,只收藏眼泪、咳嗽、叹息、笑声??所有被忽略的活着的证据。”
她怔住,随即点头:“我们可以用太阳能录音设备,每个家庭配一个,自愿参与。名字就叫……‘心音留存计划’。”
他笑了:“比我想的还暖。”
次日清晨,一封加急文件送抵基地。省民政厅批复同意设立“非营利性社区健康促进中心”,赋予独立法人资格,同时拨付首期运营补贴八十万元。随文附有一张便签,笔迹熟悉??正是那位曾公开质疑项目的副县长所写:
>**李医生:**
>我带母亲去了你们的温室。她癌症晚期,常年抑郁,那天却主动摘了一朵玫瑰别在衣领上。
>她说:“这香味让我想起嫁给父亲那天。”
>我才知道,有些东西治不了病,却能让人有尊严地走向终点。
>请继续做下去,这次,我为你们开路。
李灵拿着便签走进会议室时,正撞见林小满红着眼眶挂电话。挂断后,她哽咽道:“老师……我爸答应让我妈来参加下一期培训了。”
李灵心头一震。她记得林小满曾提起,母亲患有重度焦虑症,二十年未曾出村,连视频通话都会引发恐慌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