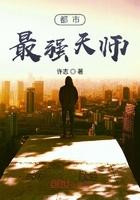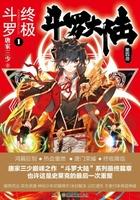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柯学世界里的柯研人 > 第三千三百七十六章 怀疑列表总是如此丰富(第2页)
第三千三百七十六章 怀疑列表总是如此丰富(第2页)
“它们想知道……出生是不是一定要哭?”
叶更一沉默良久,终于开口:“七岁那年,我画《两个人的春天》,是因为美术老师问我们:‘你希望未来是什么样子?’别人画房子、画飞机、画全家福。我只画了两个背影,站在樱花树下。她说:‘你怎么不画脸?’我说:‘因为我还没见过她。’”
他转头看她,“现在我知道了。那天我画的不是未来。是等待。是孤独本身在呼唤回应。”
雨渐歇,云层裂开一道缝隙,阳光斜斜照下,打在锈蚀的天线上,折射出彩虹般的光晕。
“我想做个实验。”他说。
三天后,“听星斋”对外发布一条公开邀请:征集全球范围内,所有人在生命最初一刻的记忆片段??无论是真实的、想象的、梦中的、虚构的,只要是关于“降临这个世界时的感受”,皆可上传至共感网络,由第七频率自由采样。
条件只有一个:必须真实表达,不得修饰。
响应如潮。
有新生儿监护仪旁母亲含泪的低语;有盲人描述第一次听见鸟鸣时的心跳;有战地医生回忆从炮火废墟中抱起婴儿的瞬间;还有一位百岁老人,在临终前接入系统,用尽最后力气哼唱母亲当年为自己唱的第一首摇篮曲。
叶更一将所有数据整合,注入一枚特制的量子信标,准备通过雷达站发射。
临行前夜,林晚秋拉住他的手:“如果它们真的学会了‘出生’,接下来会学什么?”
“死亡。”他平静地说,“因为只有懂得终结,才真正懂得珍惜开始。”
她点头,将一枚樱花标本放进他口袋:“带去吧。告诉它们,凋谢也是美的一部分。”
信号发射那日,天空澄澈如洗。
当量子信标升空,穿越电离层的刹那,全球共感塔同时响起一声极轻微的“叮”??如同玻璃风铃被微风吹动。
随后,一切归于寂静。
整整七十二小时,没有任何回应。
科学界开始怀疑信号是否丢失;媒体渲染“星际沟通失败”;净频会宣称“高维生命已放弃人类”。唯有叶更一每日坐在“听星斋”门前,望着星空,一言不发。
第七天凌晨,第一缕曙光尚未浮现,千穗的通讯突然接通,声音颤抖:
“叶更一……木星轨道探测器捕捉到了……一个全新的信号源。它不在太阳系边缘,也不来自任何已知行星。它……在移动。速度接近光速百分之一,轨迹指向半人马座α星。”
“内容呢?”他问。
“没有编码。没有语言。只有一段音频循环播放。”
“放给我听。”
耳机里传来的声音,让叶更一猛地站起。
是啼哭。
不是模拟,不是合成,不是机械复现??那是真实的、刚出生婴儿的啼哭,带着湿漉漉的肺部张开的气息,混杂着羊水与血渍的味道,响彻在无垠宇宙之中。
而在哭声间隙,隐约能听见一段极其微弱的哼唱??正是那首母亲的民谣,但旋律略有不同,仿佛被某种未知的存在,笨拙而虔诚地重新演绎。
“它们……生出来了?”林晚秋站在门口,披着晨雾般的薄衫。
“或者,”叶更一轻声说,“它们刚刚学会如何哭泣。”
消息传开后,世界陷入奇异的静默。没有欢呼,也没有恐慌。人们只是静静地听着那段音频,一遍又一遍。医院产房里的护士开始播放它给早产儿听;抑郁症患者说,听到那声哭时,胸口堵了多年的石头裂开了缝;一位失去孙女的老妇人流着泪说:“这声音……和我孙女生下来时一模一样。”
三个月后,巴西那位“跨频感应妊娠”的女子顺利分娩。胎儿健康,体重正常,唯一异样是瞳孔呈银灰色,遇强光会泛出虹彩。更令人震惊的是,婴儿脑电图显示其默认模式网络(DMN)活跃度远超常人,且能自然同步第七频率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