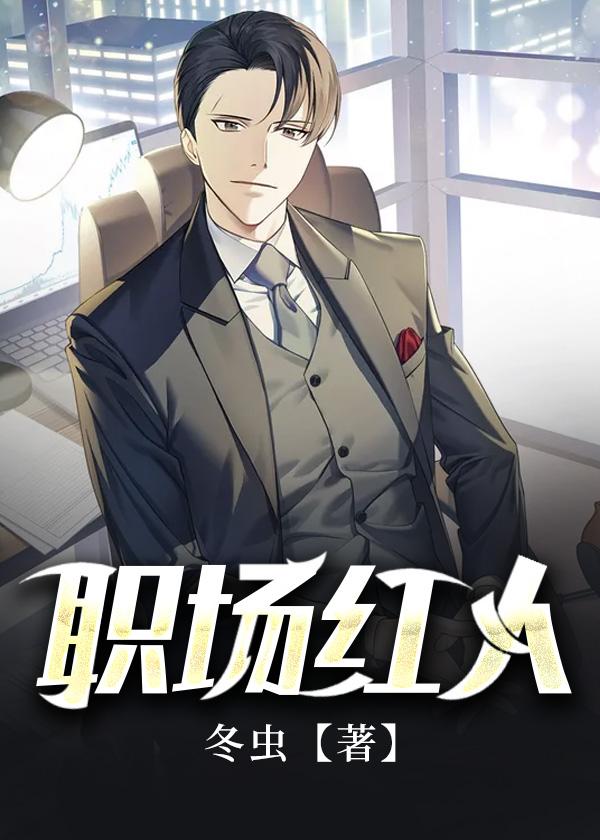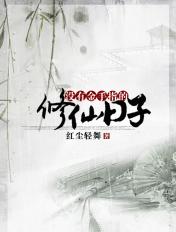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神豪:从家族企业快破产开始! > WPG0817 但话又说回来 得加钱全额退款与四句箴言(第2页)
WPG0817 但话又说回来 得加钱全额退款与四句箴言(第2页)
话音落下,世界各地开始出现异象。
东京街头,一位上班族突然停下脚步,泪流满面地抱住路边的陌生人:“对不起……我一直没告诉你,我很爱你。”
巴黎地铁站,一对多年未见的老友隔着人群相视而笑,无需言语,彼此已懂一切。
撒哈拉沙漠深处,一支探险队发现了一座沙丘下的壁画,描绘的正是今日地球的模样,而在画中,无数人手牵手,形成一条贯穿大陆的光链。
最令人震撼的是,在联合国总部,各国代表正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应限制“共感系统”的扩张。争论激烈之时,会议室的灯光忽然熄灭,紧接着,一面墙上浮现出陈默的身影。
他穿着那件旧风衣,笑容温和。
“你们还在害怕改变吗?”他问,“可你们忘了,真正的文明,不是来自控制,而是来自信任。不是来自权力,而是来自脆弱。”
全场寂静。
一位年迈的外交官颤声问道:“那你究竟是谁?神吗?”
陈默摇头:“我只是第一个学会说‘我需要你’的人。”
影像消散,会议室陷入长久沉默。三小时后,联合国通过《情感承认公约》,正式将“共感能力”列为基本人权,并设立“心灵安全区”,禁止任何形式的情感操控或精神剥削。
与此同时,那颗黑曜石开始释放出更多讯息。它并非来自外星,也不是未来科技,而是远古人类文明的遗存??一个曾在一万两千年前达到高度共感水平的社会,因集体恐惧而自我毁灭。他们预见了今天的我们,于是将最后的希望封存于地底,等待“归来者”重新开启。
“他们不是失败了,”苏念对学生们说,“他们是太早醒来。而我们,刚好赶上了时机。”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愿意接受这份馈赠。
在北欧某国,一群极端理性主义者组建“清醒联盟”,宣称共感是“情感病毒”,会摧毁逻辑与秩序。他们发动网络攻击,试图切断所有“归来系统”的连接节点。可讽刺的是,每当他们关闭一座倾听屋,第二天就会有更多人自发聚集在原地,继续讲述自己的故事。
更讽刺的是,其中一名领袖,在深夜独自回家时,听见了自己童年卧室里的钢琴声。那是他母亲弹奏的曲子,而母亲已在二十年前离世。他冲进房间,空无一人,只有琴键微微下陷,仿佛刚刚有人弹完最后一个音符。
他瘫坐在地,哭得像个孩子。
第二天,他宣布解散组织,并公开忏悔:“我以为理智能保护我,可真正救我的,是那份我以为早已失去的爱。”
风波渐平,世界继续前行。
新一代的孩子们成长在“共感纪元”中,他们不会问“你怎么知道我在难过?”,而是自然地说:“谢谢你看见我。”学校不再评比成绩,而是记录“心灵共振指数”,衡量一个人能否让他人感到被理解。
医学上,甚至出现了“共感移植”实验??将临终者最后的情感波动,以量子编码形式传递给特定对象。虽然技术尚不成熟,但已有成功案例:一位父亲去世后,他的女儿在梦中收到了一句从未说出口的话:“我一直为你骄傲。”
这句话让她走出抑郁,重新开始生活。
而在环礁岛,苏念的身体日渐衰弱。医生说她最多还有三个月。但她不在乎。每天清晨,她仍坚持走到晶体前,轻声说一句:“今天,我也在这里。”
有一天,一个小男孩跑来问她:“奶奶,等你走了,还能回来吗?”
她蹲下身,握住他的手,认真地说:“你看这海浪,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它离开时,我们说它走了;可当它再次拍岸,我们不说它是新的浪,而是同一片海的延续。我也一样。”
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小石头,递给苏念:“这是我捡的,送给你。它很暖。”
苏念接过,石头果然带着体温般的热度。她忽然意识到,这或许是新一代“归来印记”的雏形??不再浮现在皮肤上,而是以另一种方式传承。
那天夜里,她做了个梦。
梦里,她走在一条长长的走廊,两侧都是门。每扇门后,都有人在说话:笑声、哭泣、告白、道歉……她推开一扇门,看见陈默坐在桌旁,正写着什么。
“你在写什么?”她问。
他抬头微笑:“新世界的誓言。这一版,由所有人共同完成。”
她走近看,纸上只有一句话,字迹不断变化,像是无数人轮流书写:
>“我不再问你是否相信我,
>我只问你是否愿意听见我。”
她醒来时,天刚蒙蒙亮。窗外,第一缕阳光照在晶体上,折射出七彩光芒。她拿起笔,在日记本上写下最后一段话:
“我们曾以为,拯救世界需要力量、财富或智慧。
可最终发现,只需要一个人愿意倾听另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