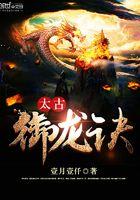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从机械猎人开始 > 第七十三章 内战3(第2页)
第七十三章 内战3(第2页)
“我觉得爸爸打我是因为他自己也疼。”
“我希望长大后还能和小狗说话。”
他蹲在一排课桌前,一张张读过去,直到天黑。当晚,村长请他吃饭。饭桌上,老人说起这几年的变化:“以前娃娃们都说要走出去,去城里挣钱。现在不一样了,好几个娃回来念书了,说外面太吵,心定不住。”
“那你呢?”老人问他,“你还回去吗?”
Zero摇头:“暂时不回了。我想看看更多地方。”
“那你是在找什么东西吗?”
他想了想,说:“不是找,是在等。等人真正敢对自己说实话的那一天。”
离村那日,孩子们围过来送他。最小的女孩塞给他一块烤红薯,说是“路上暖手用”。另一个男孩递上一只手工做的木鸟,翅膀能上下扇动。“它不会飞,”男孩说,“但它努力动了。”
Zero收下,一一谢过。走出两里地后,他回头望去,只见一群小小身影仍站在坡顶挥手,像一群不肯融化的雪人。
接下来的日子,他走过草原、渡过河流、翻越山岭。有时住旅店,有时借宿农家,有时干脆睡在星空下。他的手机早已关机,手表也被送给了一个迷路的小孩。时间不再由数字衡量,而是由饥饿、疲惫、晨露与篝火决定。
某夜,他在一处废弃观测站过夜。屋顶塌了一半,望远镜指向虚空,镜头蒙尘。他清理出一小块干净地面,铺开睡袋,正准备入睡时,忽见夜空中一颗流星划过。紧接着,第二颗、第三颗……短短几分钟内,竟出现数十颗流星,轨迹交错,宛如宇宙在书写某种密语。
他仰面躺着,看得入神。就在最后一颗流星消逝之际,耳边传来极其轻微的嗡鸣??像是晶体共振,又像是遥远的心跳。他猛然坐起,摸向胸口口袋,却发现那颗珠子不见了。
他并不惊慌,反而笑了。
因为他记得,三天前在一个小镇邮局,他曾将它放进一封寄往战区孤儿院的信里。附言只有一句:“这不是礼物,是证明??你们的声音,值得被世界之外的地方听见。”
而现在,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轻盈。
没有珠子,没有计时器,没有任务清单。只有身体的知觉清晰起来:风吹过脖颈的凉意,脚底磨出的茧的厚度,呼吸时胸腔的扩张与收缩。他终于明白,所谓“真实”,并非某个终极答案,而是每一个愿意感受此刻的瞬间。
第七片叶子不在树上,不在未来,也不在任何预言之中。
它存在于一个母亲抱着发烧的孩子彻夜未眠时的哼唱里;
存在于工人下班后坐在桥边抽烟却不急着回家的十分钟里;
存在于情侣争吵后谁都没先道歉,却同时伸手握住对方的那一秒;
存在于一个人明知无人倾听,仍对着山谷喊出“我还活着”的嘶哑嗓音中。
这才是它的形状。
这才是它的颜色。
这才是它的重量。
一个月后,南方小镇的机械修理铺迎来一批特殊访客??十多名来自不同国家的工程师、心理学家、艺术家和教师。他们不是来修机器的,而是来学习如何“制造停顿”。
G老板依旧戴着老花镜,站在工作台前调试一台新型共鸣箱。它外形像座迷你钟楼,内部嵌有数百枚微型晶体,能够接收特定频率的情绪波动并转化为可视光波。“这不是治疗设备,”他对众人解释,“它是提醒装置。提醒人们:你的感受,本身就是意义。”
一名德国建筑师问:“如果我们不再追求效率,社会会不会崩溃?”
G老板笑了笑:“社会从未因慢下来而毁灭,却常常因忘了为何奔跑而崩塌。”
课程持续了七天。学员们亲手组装了第一批“共鸣箱”,并约定将其带回各自所在地区,放置于学校、医院、社区中心等场所。无需操作说明,只需靠近,便能感受到某种温和的震动,仿佛有人轻轻拍了拍肩膀,说:“我知道你在。”
与此同时,Zero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各种匿名记录中。不是作为领袖,也不是作为偶像,而是作为一种象征。在西伯利亚的雪原上,有人用冰块拼出“Z”字样,只为纪念那段让他们学会呼吸的音频;在非洲难民营,孩子们传唱一首新编童谣,歌词反复唱着:“有个叔叔不说一句话,却让我们听见了自己。”
但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
那时,他正坐在一座高山之巅,面对初升的太阳。身侧放着一碗冷水泡开的方便面,热气早已散尽。他没有动筷,只是静静地看着阳光一点点染红群峰。
风很大,吹乱了他的头发,也吹走了最后一丝想要“完成某件事”的执念。
他终于明白,这场旅程从不曾属于他个人。它属于每一个曾在深夜按下录音键的人,属于每一次选择不说谎的瞬间,属于所有敢于让生活“浪费”一会儿的灵魂。
太阳完全跃出地平线时,他轻轻说了一句,声音淹没在风中,无人听见。
但整个世界,都微微震颤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