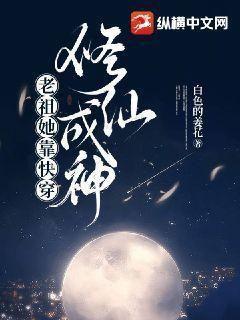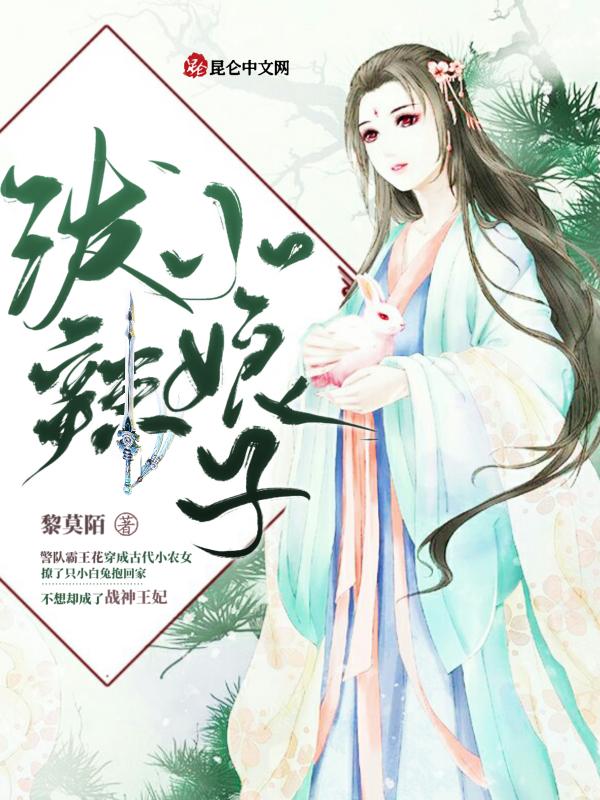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人在大明,无法无天 > 第716章 代金券引起天下重视(第1页)
第716章 代金券引起天下重视(第1页)
暮色沉沉,金陵城的街巷间弥漫着初春的湿冷。陈寒站在刑部大牢外,望着被锦衣卫押出来的几个绸缎商人,眼神冷峻如铁。
这些人面色灰败,手脚上的镣铐随着步伐哗啦作响,其中一人还在不死心地叫嚷:“大人!草民冤枉啊!那些假券都是底下人私自印的,与小人无关……”
陈寒没说话,只是从袖中抽出一叠靛青色的代金券样本,轻轻一抖。夜风拂过,券面上的暗纹在火把映照下流转如活物,与地上散落的伪造品形成鲜明对比。
“物理院的防伪纹掺了辽东朱砂,遇碱变色。”他蹲下身,将真券浸入水洼,水面立刻浮起细密的“洪武通宝”阴文。而伪造的券纸泡在水里,墨迹却晕染成一片污浊。
那商人腿一软,瘫坐在地。
“拖下去。”陈寒起身掸了掸衣摆,“按《大明律》,伪造宝钞者,凌迟。”
惨白的月光照在刑场青石板上时,朱标正在东宫翻阅奏折。烛火将他眉心的川字纹映得愈深刻,案头堆积的弹劾奏章几乎淹没鎏金笔架。
“殿下,陈大人求见。”小太监话音未落,陈寒已经跨过门槛,身上还带着刑场的血腥气。
朱标抬头,指了指桌上最厚的那本奏折:“浙江道御史联名弹劾你‘动摇国本’,说你的代金券会让百姓轻视铜钱。”
“他们当然急。”陈寒冷笑,“松江府清丈田亩的账本显示,去年市面上流通的铜钱,有三成被这些人家地窖囤着。”他从怀中掏出一本蓝皮册子,“更巧的是,这次伪造代金券的雕版,出自杭州顾氏书局。”
烛火“啪”地爆了个灯花。朱标指尖在“顾氏”二字上顿了顿——这正是浙江道御史的岳家。
“继续。”太子突然将弹劾奏折扫到地上,“明日早朝,孤要亲眼看看,还有谁敢拦着农户领券买犁!”
五更天的奉天殿前,文武百官正在寒风中呵手跺脚。突然一阵骚动,只见十几个穿粗布衣裳的农汉被侍卫引到丹墀下,他们脚上的草鞋还沾着田泥。
“这成何体统!”礼部尚书胡子直抖,“农户也配上朝?”
朱元璋的龙辇恰在此时抵达。老爷子撩开帘子第一眼就看见那帮农汉,突然咧嘴笑了:“好!朕正想听听种地的怎么说!”
朝会刚开始,户部右侍郎就捧着算盘出列:“陛下,代金券已放两省,但各府县均反映市面铜钱流通锐减……”
“放屁!”朱元璋抓起龙案上的镇纸就砸过去,“你老家江西的粮价半月跌了三成,当朕不知道?”
陈寒趁机出班,身后两名侍卫抬着个蒙布的木架:“诸位大人请看。”
红布掀开,竟是台改良水车模型。随着机关转动,水斗舀起的清水源源不断注入田垄模型,而传统水车模型旁的土地早已干涸龟裂。
“河南农户用代金券换的这水车,今春多浇了二十万亩地。”陈寒指向模型底部刻的编号,“每台补贴多少银钱,铁匠铺收了多少券,这里记得明明白白。”
都察院左都御史突然冷笑:“谁知是不是地方官虚报……”
“刘大人!”朱标突然打断,从袖中抖出一叠盖着血手印的供词,“你派去河南的师爷,可是收了当地粮商五百贯,专找用水车的农户麻烦。”
大殿死寂。朱元璋慢慢踱到那帮农汉面前,突然扯过其中一人的手:“这茧子,是扶犁磨的吧?说说,代金券好不好用?”
黑脸汉子结结巴巴道:“回、回皇上话,小人们用券换了铁犁,一天能耕八亩……”
“听见没?”朱元璋转身环视百官,声如洪钟,“这才是真正的‘国本’!”
退朝时,陈寒被工部几个官员堵在廊下。为的老员外郎压低声音:“国公爷,下官族弟在杭州有座铜矿,若代金券需要掺铜粉防伪……”
“不必。”陈寒笑着摸出张新券,券角“物理院监制”的朱印在阳光下红得刺眼,“下一批会掺琉球的海砂,遇酸显字。”
他大步走过午门时,身后传来瓷器碎裂声——某个御史气得摔了茶盏。
而远处驿道上,插着“代金券兑付”旗帜的马车,正驶向更远的州县。
第714章
秦淮河畔的茶楼里,说书人一拍醒木,满堂茶客顿时安静下来。
“列位看官,今日咱们不说那《三国演义》,也不讲《水浒传》,单说一件新鲜事……朝廷要给全天下老百姓钱!”
茶楼里顿时炸开了锅。
“钱?什么钱?”一个挑担的货郎瞪大了眼睛,手里的茶碗差点摔在地上。
说书人捋了捋胡须,从袖中掏出一张靛青色的硬卡,在众人面前晃了晃:“就是这个,代金券!凭此券可换农具、粮种,朝廷说了,绝不收回去!”
茶客们呼啦一下围了上来,有人伸手想摸,被说书人一戒尺敲在手背上:“莫急莫急,这券可金贵着呢!”
“老丈,这券真能当钱使?”一个穿粗布衣裳的农夫搓着手,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张靛青卡片。
说书人嘿嘿一笑:“浙江那边已经了,听说一个老农用这券换了把新犁,一天能耕八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