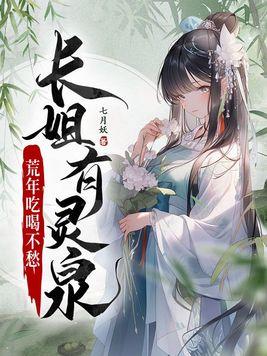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金殿销香 > 297实话(第1页)
297实话(第1页)
雨后山道泥泞,车辙深深。阿箬的马车缓缓行于江南水乡的小径上,青帷随风轻摆,帘角绣着一朵素梅,是她亲手所缝。三年来,她未曾再入城郭,只在这偏僻小镇“栖梧里”安身立命。听钟楼已成雏形,三间瓦屋围一小院,院中植一株老梅,据说是百年前某位女医隐居时所种,如今枯枝返青,春来竟开双色花??白如雪,红似血。
每日清晨六时,钟声准时响起,不响于塔,而自屋后竹林深处传出。孩子们说,那是阿婆敲的;可每回跑去寻人,只见钟架空悬,绳索微晃,仿佛刚有人离去。阿箬从不解释,只在窗边摆一张旧书案,案上放着那支银针与铜钱。她教女孩们识字、读《千字文》、背《女诫补义》,却从不许她们跪拜礼教条文。“你们要学的是思辨,不是顺从。”她说这话时目光深远,像是望着很远的过去。
这日清晨,一个瘦弱女童怯生生递上一篇习作:“阿婆,我写了首诗,你能看看吗?”
阿箬接过纸页,见墨迹歪斜却用力极深,写道:
>风吹破庙门环冷,
>夜雨煎药火微明。
>五影立墙非幻梦,
>心灯一点照孤婴。
她指尖微颤。这首诗……她记得,是当年婉柔在慈光寺抄录的一则民间歌谣残句,后来被收入《五明辑要?卷七》。一个十岁孩童,如何得知?
“你从哪里学来的?”阿箬轻问。
女童低头:“梦里有个穿灰袍的姐姐教我的。她说,我是‘续香者’。”
“续香者?”
“就是……把快要灭的香重新点起来的人。”
阿箬久久无言。她忽然想起临别那夜,四人围坐炭火旁,昭蘅曾低语:“我们这一脉,不在血脉相连,而在心火相承。”原来如此。有些记忆,并非靠文字流传,而是藏在灵魂深处,待机缘唤醒。
午后,镇东陈家送来急信:主母难产三日,稳婆束手,求“听钟楼先生”救命。阿箬即刻收拾药囊,带两名弟子前往。途中路过一片桑林,忽见树下蹲着个衣衫褴褛的老妪,正用枯枝在地上划字。走近一看,竟是《妇孺保全堂规约》第一条:“凡女子临盆,皆当以性命为先,不论出身贵贱。”
“老人家,您认得这些字?”阿箬蹲下问道。
老妪抬头,眼神浑浊却清明:“我不识字,但我娘说过,这几句,是五个娘娘定下的规矩。”
“哪五个娘娘?”
“五莲啊!她们救过我奶奶,奶奶传给我娘,我娘昨夜托梦,叫我写下来……不然以后就没人记得了。”
阿箬心头一震。她取出怀中铜钱,轻轻放在地上。老妪看见,猛地磕头:“这就是信物!和梦里一模一样!”
“您梦见什么?”
“梦见五个女人站在雪地里,一人捧书,一人执针,一人持火印,一人掌律令,最后一人……抱着个哭闹的孩子,说‘别怕,我们会回来’。”
雨又开始下了。阿箬扶起老妪,将她带回听钟楼暂避。当晚,她在灯下翻检旧稿,取出一本封皮焦黑的册子??那是火灾后唯一幸存之物,原是照雪亲笔所撰《心疗法要》,后经四人增补,称《五心通鉴》。书中记载一种古法:“情志相感,魂魄可通。若世人共念一人,则其神不散,其志不堕,纵身死百年,亦能借梦显形。”
她合上书,望向窗外。雨打梅枝,簌簌作响。那一夜,她梦见自己站在一座巨大宫殿前,金碧辉煌,匾额高悬“贞悯殿”三字。殿内无人,唯五盏长明灯静静燃烧。她走近一看,灯芯竟是由无数细小的名字编织而成??有流民、有婢女、有寡妇、有私塾先生的女儿、有被退婚仍坚持读书的少女……每一个名字都像一颗星,连成一片银河。
醒来时天未亮,但她没有再睡。她知道,这不是梦,而是一种召唤。
七日后,岭南急报传来:明心病重不起。信是她亲笔所书,字迹颤抖却坚定:“瘴气入肺,已难逆转。然保全堂尚有三百孕妇待护,我不敢去。只盼诸姐妹若闻此讯,能在同一时辰点燃一盏灯,让我知道,我不是独自走完这条路。”
阿箬读罢,泪落如雨。她立即修书飞传京师与西域。半月后,三封回信相继抵达??婉柔写道:“女子参审团今已扩至十八州,宁安旧案重审,万人联署。我将于十五夜子时,在京师贞悯祠点灯。”昭蘅信中最短:“我在疏勒河畔扎营,风沙蔽日。但今晚,我要让整支医队举火为誓。”
八月十五,中秋之夜。阿箬命人在听钟楼前设坛,燃起一盏素纱灯笼,内置五根灯芯,分别缠绕青、赤、白、黑、黄五色丝线,象征五人同心。午夜将至,全镇女孩齐聚院中,每人手持一支小烛。阿箬站在梅树下,朗声道:“今夜,我们不拜月,我们祭心。愿天下女子,无论贫富贵贱,皆得安康、自由、尊严。此愿若诚,请诸灯同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