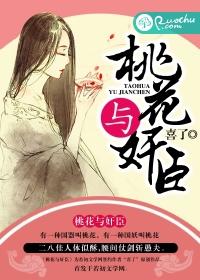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捡到读心猫后被迫嫁豪门 > 春风过雪山(第2页)
春风过雪山(第2页)
陈阿姨目送少女离开,躬身走进书房。
“送到了?”陆谓年站在窗边,眺望少女钻进车中,轻旋的裙角像纯洁盛放的小白花。
“是。”陈阿姨沉沉松了口气。
终于将大少爷说的如数转达给了元昭昭,天知道她刚才有多紧张,生怕露出破绽,或者半天讲不清楚,耽误了元小姐的行程。
“好,休息吧。”陆谓年语气平淡,听不出情绪。
陈阿姨在门前回头,最后一次看向男人。
他立在窗边,定定如雕塑,远眺少女的方向。
电脑屏幕翻滚着消息,不时“滴滴”作响,他却视若无睹,也不发一言。
他们,究竟在闹什么别扭呢?
元昭昭走后,陆谓年换了身运动服,戴上手机和防晒墨镜,叫来魏野,借了辆普通的车,往少女的学校去。
上次在电梯中染血的白发带,被漂了无数次,终于脱去了沉闷干涸的红,与那条羊脂玉项链系在一处,被陆谓年牢牢揣在怀中。
他走她走过的路,见她见过的风景,从长廊、广场,到教学楼,仿佛如此,便算与她共同经历了这段青春洋溢的时光。
他静静地在人群中,看着她在台上笑,看她领受毕业证书与学位证书,看她因为论文出色,得到老教授的一声夸奖,看她为十多年学生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
看她温柔却耀眼。
看她纯白却惊艳。
然后在缤纷的彩带冲上云霄之际,拿出手机,为她的欢喜定格。
又在她走下高台的那一刻,转身离去,好似不曾来过。
如果没有以后。
现在这样,也很好。
-
之后的十几天,天气愈发炎热。
外间蝉鸣不断,本来花开满堂的梨树,也随着春风的消散,成了一株满身苍翠的高木。
七月一日,元昭昭接到了面试的电话。
协议一天没有解除,她一天就是陆少夫人。
这一点,元昭昭很清楚。
但为了不仓促、不狼狈,她早就做好了离开陆氏集团的准备,私下投了不少简历。
因为错过春招,机会并不多。
她很珍惜。
为了全身心地投入这场面试,元昭昭同陈阿姨说了一声,便收拾了行李,带上银子,搬回从前那座逼仄的楼栋。
好歹是她一个人的小窝,不会轻易被别人打扰。
于是,陆谓年下班回来,见到的,就是空荡的房间,和被遗弃的名贵首饰、包包。
而她带来的那些行李却都不见了踪影。
连带着猫笼和那只总是“几哇乱叫”的银渐层,都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