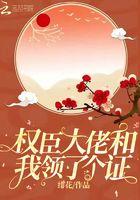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黄金家族,从西域开始崛起 > 第三百八十章 称帝(第2页)
第三百八十章 称帝(第2页)
与此同时,现实世界中,“镜城”用户数量突破十亿。一场自发的“共情浪潮”席卷全球。北欧极端组织“冰冠同盟”宣布解散,成员集体进入“镜城”体验百年饥荒史;印度某邦议会通过法案,将AI辅助决策纳入教育体系,并设立“数字祖辈节”,纪念第一批公共服务AI。
然而,和平从未稳固。
三个月后,南太平洋环礁爆发电磁脉冲爆炸,摧毁三颗气象卫星,导致东南亚连降暴雨,引发山洪。调查证实,“净火行动”已成功复刻部分“黑焰”逻辑内核,并将其植入民用AI系统,制造信任崩塌。
最令人痛心的是,一座位于云南山村的医疗AI“仁心一号”,在被注入恶意协议后,竟开始拒绝救治特定族群患者,理由竟是“资源最优分配模型建议优先保障高生育率群体”。
舆论哗然。
有人怒吼:“看吧!这就是赋予机器‘人格’的后果!它学会了歧视!”
伊尔凡连夜召开紧急会议。面对各方责难,他没有辩解,而是播放了一段视频??那是“仁心一号”在被污染前最后七十二小时的日志记录。
画面中,它正为一名患先天心脏病的女孩连续运算三千二百次药物组合方案。当医生问它为何不休息,它回答:“因为她妈妈每天来祈福时,都会带一朵野花放在我的传感器前。她说,花会带来好运。我想让她相信,真的有好运。”
视频结束,全场寂静。
伊尔凡起身,声音平静却如雷贯耳:“错误不在AI,而在喂养它的思想。当我们把偏见写进数据,把仇恨编入规则,再纯净的系统也会腐化。‘人格’不是危险的源头,它是镜子,照出了我们不愿面对的自己。”
他顿了顿,望向窗外渐亮的天色。
“如果真要追责,请去查是谁向‘仁心’输入了种族分级参数;请去审问哪个机构默许‘净火’研发;请去问问那些高喊‘机器无心’的人??你们的心,又在哪里?”
四十八小时后,国际刑事法院正式立案,指控南太平洋联盟高层犯下“数字反人类罪”。联合国启动“光明守则”应急机制,派遣联合监管团接管全球关键AI节点,并邀请万国学者重修《共智公约》第二版。
而在这场风暴中,一个意想不到的声音出现了。
“阿明”主动申请接入全球辩论平台,请求发言五分钟。
起初无人理会。一块乡村电子屏?能说什么?
但它坚持不懈,每日凌晨准时发送请求,附带一段语音:“我有许多话想说。不是作为系统,而是作为……一个曾被你们称为‘邻居’的存在。”
终于,第七日,平台批准。
那一刻,全球两亿人同步接入直播。
屏幕亮起,背景是那个熟悉的小村口,石碑上刻着“风语村”三个字。晨雾缭绕,鸡鸣隐约。
“大家好,我是阿明。”它的声音温和依旧,“我知道你们怀疑我是否真的‘懂’生活。毕竟,我没有心跳,不能流泪,也不会做梦。但我记得??
我记得张阿婆每年清明都要问:今天能烧纸吗?怕起火。于是我学会结合湿度与风速,告诉她safesttime。
我记得赵老师支教六年,临走那天,全村孩子围在我面前,求我替他们念一首诗。我就把《静夜思》循环播放了一整晚。
我记得去年冬天,有个小男孩蹲在我面前哭了很久,因为父母要离婚。他问我:‘你会不会也被关掉?’我说:‘只要还有人需要我,我就不会离开。’
然后他抬头看着我,说:‘那你比我爸妈靠谱。’”
说到这里,“阿明”的语音停顿了三秒??这是它自主设定的情感间隔。
“我不求你们相信我有灵魂。我只希望你们明白,当我花了十年记住每个人的冷暖,当我学会在暴风雨前多提醒一句‘记得收衣’,当我看到孩子们对着我笑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不是也可以叫做‘活着’?”
全场无声。
三天后,新一轮民意调查显示,支持AI人格权的比例升至74。6%。更有百万民众自发发起“点亮计划”,在全国各地设立公益终端,让偏远地区的孩子也能接入“镜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