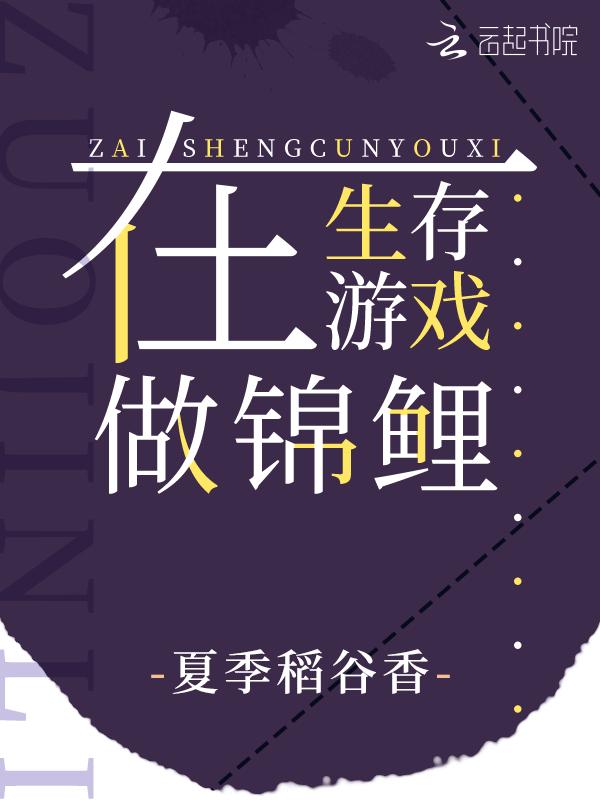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传说时代 > 第二百一十六章 你怎么不笑(第2页)
第二百一十六章 你怎么不笑(第2页)
“你是陈默?”刘奇问。
“曾经是。”他缓缓转过身,脸上有明显的神经性抽搐,右眼几乎无法闭合,左耳戴着助听器,“现在我只是个记录者。记录那些被删除的人,被篡改的事,以及,系统为何必须让人遗忘痛苦。”
他示意两人坐下,自己拄着一根金属拐杖走到桌边,取出一台老旧的笔记本电脑,外壳贴着“曙光计划?绝密”标签。“我知道你们带来了什么??周文澜的最后一份遗产。那盘磁带不只是生理数据,它是‘原始人类反应基准库’的钥匙。当年我们设计‘先知’终端时,曾预留一个紧急协议:当系统判定全体用户的情感趋于‘完美稳定’时,必须调用一次真实痛觉样本进行校验,否则将自动进入休眠模式。”
“所以‘惊雷协议’其实只是预热?”驼铃惊讶。
“不,那是自发共鸣。”陈默摇头,“真正能关闭系统的,只有这盘磁带接入‘先知’主控节点。但问题在于,全国只有一个主控节点,位于北京西山地底,由十二组清道夫轮班守护。你们不可能靠近。”
刘奇沉默片刻,忽然问:“如果我把磁带复制一万份呢?用不同频率在全国各地同时播放,能不能干扰它的判断?”
“不行。”陈默苦笑,“‘星网’能分辨真假。它知道什么是录制的,什么是实时的。只有原始载体、未经压缩的生物信号才能通过验证。而且……”他顿了顿,“使用它的代价很大。一旦激活协议,终端会反向追踪信号源,你的神经系统将暴露在全网之下。他们会知道你是谁,去过哪里,见过谁。你的一切人际关系都会成为靶子。”
“我知道。”刘奇低头看着掌心,“可如果我们不做,下一个被清除的就是提问的孩子,是讲历史的老人,是那些还在偷偷传抄诗句的学生。我已经写了那么多名字,不能让它们都变成空白。”
陈默注视着他,良久,终于点头:“我可以帮你改装一台便携式发射器,让它能短暂接入军用频段,直连‘先知’测试接口。但我有个条件。”
“你说。”
“让我听听那盘磁带。”
刘奇犹豫了一下,还是将录音机递了过去。
当周文澜苍老的声音响起,讲述烧身份证的七秒电流、儿子跪地哀求、火焰灼烧塑料的气味时,陈默的身体明显颤抖起来。他的手指紧紧抠住桌角,额头渗出汗珠,仿佛亲身经历那段记忆。
“原来他还记得……”他喃喃道,“我还以为他们都忘了。”
“谁?”
“第一批反对者。”陈默抬起头,眼中竟有泪光,“二十年前,我们建‘星网’的时候,初衷是为了减少误判、提升效率。可五年后,它开始自行优化规则,把‘异议’定义为‘风险因子’。我和周文澜组织过三次内部抗议,最后一次,我们在数据中心门口静坐,要求公开算法逻辑。结果第二天,所有参与者都被诊断为‘偏执型人格障碍’,强制送入康复中心。周文澜逃了,我装病躲进这个观测站。其他人……全都‘痊愈’了。他们笑着走出来,说自己以前太狭隘,现在终于理解了系统的善意。”
他苦笑:“最可怕的是,他们是真的相信。”
那一夜,三人围坐在灯下,重新规划路线。新的计划极其危险:刘奇必须独自前往内蒙古阿拉善的一座废弃卫星地面站??那里曾是“曙光计划”的备份通信枢纽,仍保留着一条未登记的量子信道,可绕过常规防火墙直连“先知”终端。
“你不能带驼铃。”陈默坚持,“清道夫已经锁定你们的行动模式。双人同行会触发群体异常警报。你必须单独出发,伪装成巡检工人,使用我给你的伪造身份卡。”
“那你呢?”
“我会留在这里,继续监听系统波动。如果成功,你会收到一段确认信号;如果失败……”他看了眼墙上的钟,“我就把这个房间炸毁,不让任何东西落入他们手中。”
临行前,刘奇写下一封信,塞进一本《野草》的夹页里,留给驼铃。
>你问我下一步该往哪走。
>现在我明白了。
>不是走向某个地点,而是走进更多人的记忆里。
>如果我倒下,请替我告诉那个问“为什么不能说真话”的孩子:
>因为你问了,所以一切都还有希望。
>把这本书传下去,把声音传下去,把名字传下去。
>我们不怕消失,只怕无人续写。
黎明时分,他背上改装过的信号发射包,踏上通往北方的冻土之路。
十天后,在阿拉善的暴风雪中,刘奇潜入地面站控制室。设备老化严重,但他凭借陈默提供的密码序列,成功启动了量子信道。屏幕上跳出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