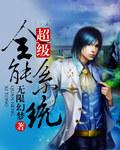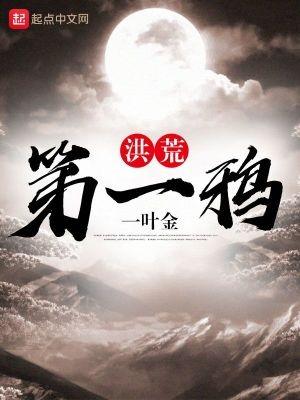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华娱从洪世贤开始 > 第622章 军事机密不方便透露哈(第2页)
第622章 军事机密不方便透露哈(第2页)
林浩然怔住了。他猛地翻开随身携带的档案袋,从中抽出一张泛黄的照片??那是他在整理马占奎遗物时发现的一叠旧资料之一。照片上,五名年轻科研人员站在雪山前合影,中间那位扎着麻花辫的女子,正是录音中的声音主人。
姓名栏写着:**周文清,江苏苏州人,1945年生,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师**。
而她的妹妹林晓梅……正是林浩然的母亲。
“妈从来没提过她有个姐姐。”他喃喃自语,眼眶发热。小时候母亲常讲起外公早逝、外婆病重,家里被迫送走一个孩子换粮救命的事。但他一直以为那位姑姑死于饥荒,没想到她竟成了国家秘密测绘计划的一员,最终埋骨雪山。
“原来你是我的姑母。”他对着洞口轻声道,“我替妈妈来看你了。”
挖掘工作全面展开。由于地形险峻,重型设备无法进入,只能采用人工掘进结合微型机器人探路的方式。每一铲土都小心翼翼,生怕惊扰了沉睡的灵魂。
第三天傍晚,第一具遗体被发现。蜷缩在角落的行军床上,身上盖着褪色的军毯,手里还攥着一支钢笔。身旁放着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封面写着:“K-9站终版地形图(手绘)”,背面密密麻麻标注着经纬度、海拔、冰川移动轨迹。
法医初步判断,死亡时间约为二十年前。
随后两天,又陆续找到另外两具遗骸,分别属于男性技术人员和一名女护士。他们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仍在坚持记录数据,并尝试用自制无线电向外界发送信息。可惜信号太弱,始终未能传出大山。
直到第七天清晨,当最后一段通道被清理完毕时,所有人都愣住了。
主舱中央,坐着一个人。
准确地说,是一个老人。白发如雪,面容枯槁,双眼紧闭,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胸前别着一枚铁道兵徽章??编号与马占奎那一枚完全一致。
他的双手放在一台老式打字机上,指尖僵直,仿佛刚刚敲完最后一个字符。
而在他面前的桌上,摆着一台仍在运转的短波发报机,指示灯规律闪烁,每隔十分钟发出一次固定频率的信号。经解码后确认,内容竟是连续不断的经纬度坐标,精确到小数点后六位,覆盖整个青藏高原东部区域。
“这是……实时更新的地图数据?”小李难以置信,“这台机器怎么可能运行半个世纪?”
老周仔细检查电源系统,终于在墙体夹层中发现了秘密:一组串联的手摇发电机与蓄电池组,连接着一根深入岩层的地下水管道。每当水流通过涡轮转动,便能产生微量电力,勉强维持设备运行。而最关键的是??有人定期维护它。
“他还活着。”林浩然低声说,“这个人,一直在替他们活着。”
话音未落,老人忽然微微颤动了一下眼皮。
众人屏息凝神。几秒钟后,他缓缓睁开眼睛,浑浊的目光扫过这群陌生人,嘴唇微动,发出沙哑至极的声音:
“你们……终于来了。”
接下来的七十二小时,成为医学奇迹与精神史诗交织的时刻。老人名叫**陈国栋**,原属铁道兵后勤支援科,1971年参与澜沧江大桥抢修任务,是赵振山团队的物资协调员。桥基塌方时,他恰好外出运送零件,侥幸逃生,却被困于雪线之上,靠啃食树皮活了下来。
三个月后,他循着无线电波找到了K-9气象站。那时三位科学家尚未去世,但他们已无力走出大山。于是陈国栋做出了选择??留下。
“他们教会我读气象图、校准仪器、修复电路。”他在病床上回忆,声音虚弱却清晰,“我说我要替你们走下去。哪怕只有一口气,也要把数据送出去。”
此后的五十年里,他独自守护这座地下站,每年徒步上百公里采集周边环境变化,手工誊抄数据,定时发送。食物靠狩猎和采集,药品靠翻越山岭换取。他曾三次遭遇雪崩,两次险些冻死,但从未放弃。
“我知道没人会听见。”他说,“但我必须发。因为总有一天,会有人来听。”
病房里一片寂静。张秀英握着他布满老茧的手,泪水滑落:“您为什么不早点求救?为什么不说自己还活着?”
老人笑了笑:“我不是为自己活着。我是为他们活着。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任务完成了。”
一个月后,国家正式追授K-9气象站全体成员“卓越科学贡献奖”,并将他们绘制的手绘地形图作为珍贵文物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同时,基于陈国栋提供的完整气候数据库,中科院发布了首份《青藏高原五十年生态演变报告》,引发国际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