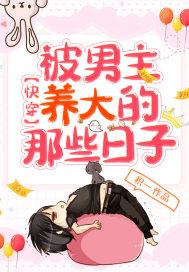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这阴间地下城谁设计的 > 第七百七十七章 又见内在潜力(第2页)
第七百七十七章 又见内在潜力(第2页)
他伸出手,掌心浮现出一颗微小的光核,宛如浓缩的星云。“这是我最后能留给这个世界的东西。它不储存记忆,而是激发‘记得’的能力。任何人接触它,都能短暂地感知到他人的情感重量??哪怕对方早已不在。”
“你要把它交给谁?”她问。
“交给你。”他说,“你是第一个读懂《未焚之书》的人,也是唯一一个既承载记忆、又敢于释放它的人。林奶奶选你,不是偶然。”
她接过光核,入手温润,仿佛握着一颗仍在跳动的心脏。刹那间,无数画面涌入脑海:一位母亲抱着夭折婴儿彻夜哭泣;一名战士在战壕中写下最后一封家书;一个孤独的老人每天给亡妻的墓碑读报……这些都不是她的记忆,却是她能感同身受的痛。
“我会把它带到学校、医院、养老院、孤儿院……”她低声说,“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听见’。”
林小远看着她,眼中闪过欣慰:“那么,我的任务完成了。”
话音落下,他的身影开始变得透明,忆质晶体从皮肤剥离,升腾为空中漂浮的光尘。风一吹,便散向四方。
“等等!”她伸手想抓,却只握住一缕微光。
他最后的声音随风而来:“告诉所有人……别怕记得。因为爱,从来不怕被提起。”
然后,他消失了。
没有爆炸,没有轰鸣,只有钟楼顶端那一声悠长的铃响,仿佛送别,又似迎接。
第二天清晨,忆堂门前聚集了许多人。
有快递员、学生、老人、医生、艺术家……他们互不相识,却都做了一件事:在门口放下一件物品??一封信、一张照片、一首手写的诗、一段录音、甚至是一块糖果的包装纸。每样东西旁边都附着一张纸条,写着:“请让更多人记得。”
陈雨眠站在二楼窗口,静静看着这一切。她手中捧着那颗光核,已被封装进一枚透明水晶吊坠,挂在胸前。每当有人靠近忆堂,吊坠便会微微发亮,像是感应到了某种频率。
中午时分,联合国特派代表抵达第七城,宣布将“共情档案库”升级为“全球记忆共同体”,并邀请陈雨眠担任首席记忆传承官。她没有立刻答应,而是反问:“你们愿意公开管理者的所有数据吗?包括他们封锁的记忆、删除的姓名、抹去的故事?”
代表犹豫片刻,终是点头。
“那我可以考虑。”她说,“但条件是,今后不再有‘禁止回忆’的名单。所有记忆,无论痛苦或美好,都应拥有被讲述的权利。”
当天下午,第一批被解禁的记忆公之于众。其中一段视频震动世界:上世纪六十年代,一名黑人女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成功激活忆质反应,却被上级以“情绪不稳定”为由剥夺成果,并强制遗忘相关经历。她在日记中写道:“他们以为删掉我的名字就能抹去真相,可我的女儿会记住,我的孙女会传下去,总有一天,这颗种子会发芽。”
视频发布两小时内,全球超过百万女性科研工作者自发上传自己的工作日志,形成一场“记忆接力”。
夜晚再度降临。
陈雨眠独自回到初城遗址,在祭坛前点燃一支新蜡烛。火焰跳跃,映照出石板上那句“建城者必先失所爱”。她轻轻抚摸那行字,低声说:“我现在懂了。林奶奶失去儿子,所以建城;林小远失去自己,所以成为门;而我……也曾失去父母,在孤儿院长大,所以才如此害怕遗忘。”
她闭上眼,将水晶吊坠贴在石板上。
刹那间,整个祭坛亮起蓝光,忆质晶体共振鸣响,如同万千人在同时低语。地面裂开一道缝隙,从中升起一座小型方碑,碑面空白,却隐隐浮现文字轮廓。
她知道,这是新的《未焚之书》分支,专属于初城的源头之碑。
她取出笔,在碑上写下第一句话:
>“真正的地下城,从不藏在地底。”
>“它生长在每一次选择记住的瞬间。”
>“在这里,死者说话,生者倾听。”
>“在这里,爱不会终结,只会不断重生。”
字迹落定,碑体轰然震动,光芒顺着地脉扩散,与全球各地的记忆锚点相连。从此以后,任何人在任何地方真诚地讲述一段被遗忘的故事,初城的石碑都会微微发烫,仿佛回应。
数日后,世界各地陆续出现奇异现象:
冰岛一座休眠火山口喷发出带有荧光颗粒的烟雾,经分析,竟是由亿万个微型忆质晶体构成,飘散后融入雨水,当地人称“记忆之雪”;
撒哈拉沙漠夜间浮现巨大光影,勾勒出古代商旅队伍的轮廓,伴随驼铃与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