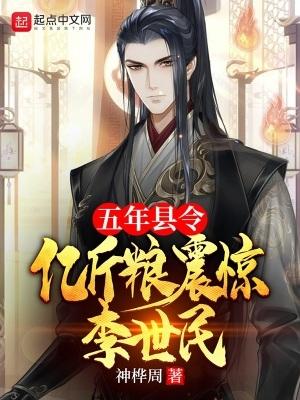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都重生了,我当然选富婆啦! > 第434章 荣念晴 嗯6k求订(第1页)
第434章 荣念晴 嗯6k求订(第1页)
吕尧跟王大老板说这么多,其实本质的目的不是待价而沽,又或者像王大老板想的那样,看看将来这位王大老板能不能给他兜底……好吧,确实也有这方面的意思。
但是呢,吕尧对自己的定位也非常的清晰,他做的事情。。。
雪化了,春未至。城市在融冰的湿气中苏醒,屋檐滴水如钟摆,敲打着吕尧生活的节奏。他站在阳台上晾晒母亲留下的旧毛衣,羊毛已泛黄,袖口磨出了毛球,却仍散发着淡淡的樟脑味??那是她去世前最后一个冬天亲手叠进衣柜的。他轻轻抚过针脚,忽然听见楼下传来熟悉的脚步声,不疾不徐,带着一种近乎仪式感的沉稳。
是陈素芬老师。
她撑着一把墨绿色的油纸伞,怀里依旧抱着几本作业本,但这次封面写着“火种回音计划?第三期”。她抬头看见吕尧,笑了笑,没说话,只是扬了扬手中的本子。吕尧点点头,转身下楼开门。
“又来了?”他接过本子,指尖触到纸张的粗糙感。
“这次不一样。”陈素芬抖了抖伞上的水珠,走进屋,“孩子们开始写‘声音日记’了。不是采访别人,而是记录自己。有个孩子说:‘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至少我的声音还在。’”
吕尧心头一震。他翻开第一本,字迹稚嫩却用力:
>“今天爸爸喝醉了,摔了碗。妈妈躲在厕所哭,我没敢出声。可我在‘时间信使’里录了音。老师说,只要存下来,就没人能抹掉它。我不怕了。”
第二本里夹着一张打印的语音波形图,旁边贴着一行小字:“这是我奶奶的声音。她说她年轻时被批斗,整整三年没说过一句话。现在她每天对着手机讲一段,像补课。她说:‘我把沉默的年头,一天天还回去。’”
吕尧翻到最后一页,停住了。那是一封未寄出的信,署名是一个叫李小满的女孩,十二岁:
>“吕老师,我妈妈上周走了。她是环卫工,凌晨扫街时被车撞了。警察说司机逃逸,监控坏了。可是我在她手机里找到了一段录音??她每天上班前都会说一句:‘今天也要好好活着啊。’那天早上,她也说了。我就把她这句话上传到了‘呼吸频道’,编号是#1,275,088。现在有三万多人听了,有人留言说,这是他们听过最勇敢的话。我想让全世界都知道,她不是无名之辈,她是个会对自己说加油的人。”
吕尧闭上眼,喉咙发紧。他知道那段录音。就在昨天深夜,他在后台巡查时看到数据异常飙升,点进去才发现,短短八小时内,这条仅六秒的语音被转发了十七万次,评论区堆满了“她值得被记住”的留言。有人自发发起募捐,为她母亲立了一块刻着语音二维码的纪念牌,插在事发路口的花坛边。扫码就能听见那个温柔而坚定的声音:“今天也要好好活着啊。”
他睁开眼,轻声问:“小满呢?”
“她在学校心理辅导室,不肯回家。”陈素芬声音低下去,“她说,家里没了妈妈的声音,太安静了。”
吕尧沉默片刻,起身打开电脑,调出“时间信使”的管理界面。他输入编号#1,275,088,点击“设为永久守护音频”,并附加一条系统公告:
**“此声音已被百万用户共同见证。无论技术如何更迭,它将永远存在于‘火种’的记忆体中。”**
他又新建一个项目,命名为“遗声计划”??专为那些因意外、暴力或不公而突然中断的生命,保存他们最后的话语,并通过AI还原其语言习惯,生成简短的“未竟之言”,供亲人聆听与告别。他不想让任何人再经历那种“话没说完,人已不在”的撕裂。
“告诉小满,”他说,“她妈妈的声音,已经变成了星星。只要有人愿意听,它就不会熄灭。”
陈素芬看着他,忽然笑了:“你知道吗?有些家长开始反对孩子参与这些活动。他们说,你们这是在教孩子‘惹事’。有个父亲直接冲到学校,吼着要我们删掉他儿子关于校园霸凌的录音。”
“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如果你不让孩子说话,那他将来只能用拳头或药片来表达痛苦。’”她顿了顿,“然后我把《公民表达与社会倾听》教材拍在他桌上,说:‘这是国家规定的课程内容,请您先读完再决定要不要反对。’”
吕尧忍不住笑出声。可笑声未落,手机震动起来。是扎西。
视频接通,背景是一间昏暗的地下工作室,墙上贴满地图和人物关系图,中央一台老式收音机正播放着缅甸语新闻。
“我们找到‘普妹计划’的第一个海外落地点。”扎西压低声音,“泰国清迈的一所难民营学校,已经开始培训Rohingya女童使用‘声音指纹’技术记录家园毁灭的过程。她们把录音藏在经书里,带过边境。”
“风险太大。”吕尧皱眉。
“可她们说,比起失语,死亡都算轻的。”扎西眼神锐利,“更重要的是,我们刚收到一条来自云南边境的匿名上传??一段军用频段的截录音频,内容涉及某地警方对‘火种驿站’志愿者的定点监控指令。发送者用了三层跳转和声纹伪装,但我们用新算法反向追踪,发现信号源头竟来自省内某政法委内部网络。”
吕尧瞳孔骤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