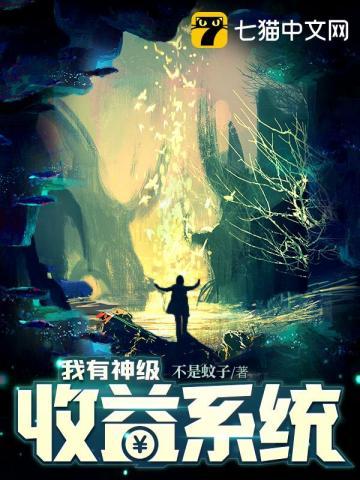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华娱情报王 > 380 华谊少了一个祸害乐视添了一员猛将(第1页)
380 华谊少了一个祸害乐视添了一员猛将(第1页)
“矮子,找茬是吧?”
看着和霍丝燕聊的火热的张馨雨,王欧皱了皱眉头,待张馨雨离开后,直接质问霍丝燕。
“聊天你也管,你别叫同心姐了,叫?嗦姐吧。”
霍丝燕收起刚和张馨雨交换联系方式的。。。
夜色再次降临,城市灯火如星河铺展。黄枝坐在书桌前,窗外的风轻轻掀动窗帘一角,像某种无声的提醒。他刚结束一场长达五小时的内部复盘会,团队将庭审全程拆解成三百七十二个节点,逐一校验“清源”在证据生成、数据加密与司法对接流程中的每一个技术细节。结果令人欣慰??无一失误。
但他知道,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手机震动,是林晓发来的语音:“法院今天收到了三封匿名举报信,内容全是针对‘清源’系统涉嫌‘操控舆论导向’和‘未经许可采集用户行为数据’。”她顿了顿,“虽然已被驳回,但有人在试图把水搅浑。”
黄枝没有立刻回复。他打开电脑,调出“百日千村计划”的实时地图。一千个村庄中,已有六百四十三个完成部署,培训记录累计超过一万两千人次。屏幕上跳动的绿色光点如同星星之火,缓慢却坚定地蔓延向那些曾被信息洪流遗忘的角落。
他忽然想起黔东南那个苗寨里的阿婆。那天临走时,老人执意塞给他一双亲手绣的布鞋,说:“你们不是官家人,可做的事比当官的还实在。”那一刻,他几乎哽咽。这双布鞋现在就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旁边是一本翻旧了的《民法典》和一张陈婉生前主演电影的剧照。
第二天清晨,董萱带着念真去了幼儿园。孩子最近迷上了“真相小卫士”的角色扮演,每天都要用玩具手机对家里的每一条短信进行“查证”。黄枝送他们出门时,念真突然回头问:“爸爸,如果坏人学会了假装‘清源’,我们还能相信谁?”
这个问题让他怔住。
回到家中,他拨通了于征的电话:“启动‘镜渊工程’。”
这是他们私下讨论已久的一个项目??构建一个反向验证机制,专门识别伪造的“伪清源报告”。近年来,已有不法分子利用截图工具伪造查证结果,用于敲诈或洗白。更危险的是,境外某些组织已经开始训练AI模型,批量生成外观高度相似的技术文档,甚至连时间戳和数字签名都能模拟。
“我们不能只做真相的发布者,”黄枝说,“还得教会世界如何辨别真假的‘真相’。”
于征沉默片刻:“这意味着我们要公开核心算法逻辑的一部分。”
“那就公开。”黄枝语气平静,“真正的安全不在封闭,而在透明。只要我们经得起scrutiny(审查),就不怕任何人挑战。”
当天下午,“清源”官网发布一则技术公告:即日起开放“电子证据溯源协议v1。0”标准框架,并邀请全球开发者参与审计。同时上线“镜渊测试平台”,允许任何个人或机构上传疑似伪造的查证报告,由系统自动比对哈希值、证书链与传播路径,十分钟内返回鉴定结果。
消息一出,国内外技术圈震动。
有支持者称这是“中国科技界罕见的开放勇气”,也有质疑声认为“此举等于暴露软肋”。某知名网络安全博主发文警告:“一旦敌对势力掌握验证逻辑,反而可能加速进化攻击手段。”
黄枝在微博回应:“如果你的房子建在沙地上,风吹就会倒;如果你的房子建在岩石上,风暴只会让它更坚固。我们不怕检验,因为我们从不说谎。”
一周后,第一起通过“镜渊”识破的案件浮出水面。一名男子持伪造的“清源报告”向企业勒索五十万元,声称掌握了对方高管的贪腐证据。企业报警后,警方通过测试平台确认报告为假,迅速破案。该案例被公安部列为典型,纳入全国网安培训教材。
与此同时,“百日千村计划”进入攻坚阶段。第十支队在甘肃陇南遭遇极端天气,山路塌方导致设备运输中断。志愿者们不得不徒步八小时背负服务器进村,在临时搭设的帐篷里完成了系统安装。当地一位乡村教师含泪写下日记:“以前学生转发‘某地地震伤亡惨重’的消息,我只能靠直觉劝阻;现在,我们可以一起打开‘清源’,看着它一步步拆穿谎言。”
这些故事开始在网络上传播,没有煽情标题,也没有流量包装,却悄然汇聚成一股暖流。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主动学习信息验证技能。一所中学甚至将“识谣能力”纳入选修课,教材里引用了念真画的那幅“小男孩举着发光手机”的涂鸦。
然而,暗流仍在涌动。
某晚,黄枝接到国家网信办某位熟识官员的私信:“高层对‘清源’的社会影响力感到警惕。有人提出,应将其收归国有,由指定单位统一管理。”后面还加了一句,“这不是命令,只是预警。”
他盯着屏幕良久,最终回了一个字:“谢。”
他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一个能影响千万人认知的工具,不可能永远游离于体制之外。关键在于,如何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赢得制度的信任。
三天后,他主动提交了一份《关于“清源”系统治理架构优化建议书》,明确提出三点:一、成立独立的“清源公益理事会”,由法律、技术、伦理领域专家组成,负责监督系统运行;二、所有核心代码继续开源,接受第三方年度安全审计;三、自愿将系统纳入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名录,接受监管但拒绝行政干预具体运营。
这份文件像一枚精准投下的棋子,在各方势力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晰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