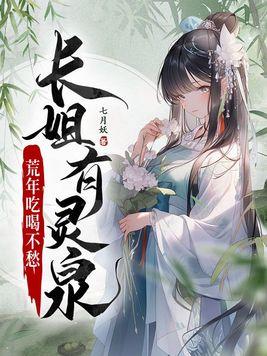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我的低保,每天到账1000万 > 第609章 我不是月嫂(第3页)
第609章 我不是月嫂(第3页)
他知道,这不是科学能解释的现象。也许,是无数失去亲人的人类集体意念,在某个维度形成了共振;也许,真是那个年轻人的灵魂穿越时空完成了最后一次通话;又或者,这只是大脑在极度渴望下产生的幻觉。
但他不在乎。
重要的是,有人听见了。
三天后,迷彩场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声音展览”。周老带来了他孙子听醒的那盘磁带,女孩带来了她母亲的MP3,老头带来了那台收到“回信”的收音机。还有更多陌生人闻讯而来:一位母亲带来女儿车祸前最后录制的日记音频,一名退伍军人带来战友牺牲前哼唱的军歌片段,甚至有个盲童带来他自己用口哨模仿鸟鸣的录音。
林晚把所有设备连接在一起,接入共感网络主干道。午夜十二点整,他按下总控按钮。
刹那间,屋顶铜线剧烈震颤,如同千万根神经同时苏醒。电报机疯狂吐出纸带,内容不再是代码,而是一句句话语,来自世界各地:
“我也失去了弟弟。”
“我丈夫走的那天也在下雨。”
“谢谢你让我知道我不是唯一一个还在等的人。”
而在所有信号交汇的中心,浮现出一段全新的旋律??由数百种不同语言、不同音色、不同情绪交织而成的合唱。它没有歌词,却比任何歌曲都更接近“思念”本身。
展览持续了七天。第七天晚上,林晚独自坐在院子里,看着记忆树在月光下投出长长的影子。忽然,他听见一阵脚步声。
回头一看,是念念。
她背着行囊,脸上晒得微黑,头发扎成乱糟糟的辫子,手里拎着一只竹筒。看见他,她笑了,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那是小时候爬树摔的。
“我回来了。”她说。
林晚没说话,走过去,轻轻抱了抱她。
“我把声音种得很远。”念念靠在他肩上说,“不止云南,我还去了贵州、广西、西藏……每个村子,我都录下一首老人唱的歌。他们说,这些歌再没人教了,唱完就没了。但现在,它们都在共感库里活着。”
林晚点头。
“你知道吗?”念念仰头看他,“有个九十岁的奶奶听完我们转发的童谣,哭了。她说,那是她妹妹五岁时唱的,后来妹妹病死了,这首歌也就失传了。可现在,它回来了。”
林晚摸了摸她的头。
“所以你说得对。”念念轻声说,“修东西不是为了让它能用,是为了让曾经的心跳,还能被人听见。”
夜风拂过,记忆树的叶子簌簌作响。徽章在月光下泛着幽光,像一颗永不熄灭的星。
林晚走进厨房,重新点燃灶火。
锅里的水再次沸腾。
他说:“今天炖汤吧,加点念念带回来的野菌。”
蒸汽爬上窗棂,模糊了外面的世界。而在某处深空,Echo-9信号源正缓缓转动,继续播送着那首童声版《茉莉花》,一遍,又一遍。
仿佛在说:
听见了吗?
我一直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