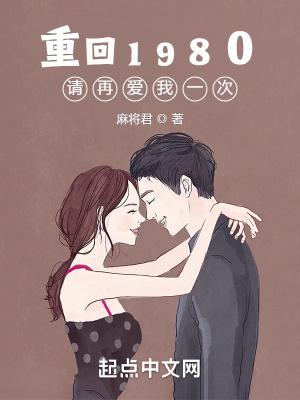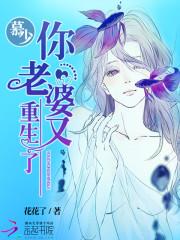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谁说我是靠女人升官的? > 327臣请陛下给予杀人权(第3页)
327臣请陛下给予杀人权(第3页)
三天后,守问堂门前支起一口青铜巨鼎,据说是上古时期用于祭天的礼器。禾生带领百名耕者,将历年保存的老种子一一取出:红米、紫麦、黑豆、黄粟、青稞、白薯、蓝葵……共计九十九种,皆为濒临灭绝的原始品种。
他们在鼎中加水,慢火熬煮。
七日七夜,火不熄,人不眠。
第八日清晨,汤成。色泽浑浊,气味朴拙,无香无艳,唯有一股大地深处的气息弥漫开来。
禾生端起一碗,走向村口。
那里早已聚集数千人,有观望者,有嘲讽者,也有真正饥饿的流浪汉。他站在石台上,高声道:
“这不是药,不是仪式,也不是抗议。这是一顿饭。一顿由一百个人种了整整一年,才换来的一碗杂粮粥。”
他喝下第一口,缓缓咀嚼,然后闭眼,泪水滑落。
“我尝到了奶奶的手温,父亲的汗水,妹妹最后的笑容……还有,那些连名字都没留下的陌生人,他们饿着肚子,却把最后一粒种藏在鞋底,传了下来。”
他睁开眼,看向人群:“你们愿意试试吗?”
起初无人响应。直到一名衣衫褴褛的老农走上前,颤抖着接过碗,喝了一口,突然跪地痛哭:“这是我娘的味道啊……我以为这辈子再也喝不到了……”
一个接一个,人们排起长队。
就连伪装成记者前来讥讽的网红,喝完后也摘下摄像机,哽咽道:“我拍了五年‘奢华美食’,可从来没有哪顿饭,让我觉得自己是个活人。”
当天夜里,全球十二个国家的社交媒体同时爆发出同一句话:
>**“我想吃一顿真的饭。”**
三个月后,联合国召开第二次“劳动尊严峰会”。会议现场,各国代表面前不再摆放精致餐点,而是一碗热腾腾的杂粮粥。主持人宣布:“从今日起,‘真实饮食权’列入基本人权条款。任何国家不得以效率、科技或便利为由,剥夺人民亲手种植、共同烹煮、围坐分享食物的权利。”
而在守问堂,李砚之终于归来。
他带回敦煌壁画新显的文字,经学者破译,竟是四句诗:
>**“笔断意不断,
>土枯心不枯。
>万人同耕处,
>即是归家途。”**
他将诗刻于问田中央的石碑上,又在碑后种下一株新苗。
禾生问他:“这次种什么?”
“不知道。”李砚之微笑,“但它一定会告诉我们。”
那一夜,北斗锄星格外明亮。风铃响了整整一夜,仿佛天地都在低语。
禾生躺在屋顶,望着星空,忽然听见田里传来细微声响。他起身查看,只见所有薯苗的叶片背面,同时浮现出一行字,如同千万人齐声书写:
>**“谢谢你,还记得我们。”**
他蹲下身,用手掌覆住泥土,轻声回应:
“以后每一顿饭,我都会替你们多吃一口。”
远处,一轮朝阳正缓缓升起,照亮了连绵的田埂,照亮了蜿蜒的小路,照亮了无数双正在握紧锄头的手。
大地无言,却始终在说:
**“我在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