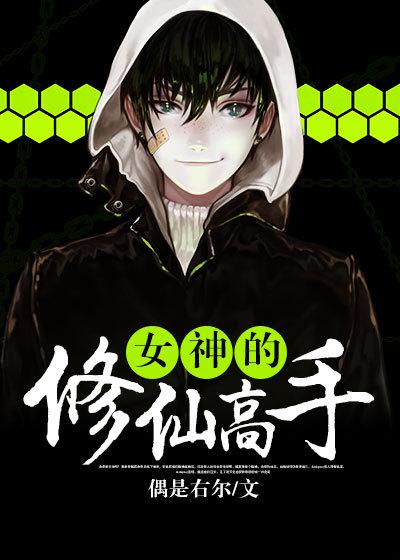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谁说我是靠女人升官的? > 328上岸第一刀先砍女帝(第3页)
328上岸第一刀先砍女帝(第3页)
禾生愣住。
次日清晨,他召集所有人,宣布:“我们要办一场‘万人忆食宴’。不用邀请函,不设门槛,只要愿意讲述一段与食物有关的真实记忆,就能来吃一顿真正的饭。”
消息传出,应者如潮。
一个月筹备期里,来自全国各地的耕者自发送来种子、工具、柴薪;厨师协会派出志愿者团队;铁路工人组织专列接送偏远地区的老人;甚至有监狱服刑人员集体写信请求参与,说“我们也想学会好好吃饭”。
宴席当日,守问堂外搭起三百张长桌,绵延数里。锅灶林立,烟火升腾。主厨是由一百零八位母亲组成的“忆味团”??她们带来的不是名菜,而是各自孩子小时候最爱吃的家常饭:野菜糊糊、红薯稀饭、腌萝卜配糙米饭……
开席前,禾生站在高台上,举起一碗清水。
“这碗水,来自第一代耕者的汗,来自妹妹临终前舍不得喝的那一口,来自母亲熬夜织布时润喉的凉茶。今天我们不敬神,不拜官,只敬那些饿着肚子把种子藏下来的人。”
他将水洒向大地。
全场肃立。
然后,第一位客人走上台??是个穿校服的女孩,声音很轻:“我爸爸车祸去世那天,早餐是他给我煎的蛋。他说‘多吃点,考试才有劲’。后来我一直不敢吃煎蛋……今天,我想试试。”
她接过一碗小米粥,旁边配着一小碟焦香鸡蛋。吃下第一口,泪如泉涌。
接着是一位退伍老兵:“我们在前线啃压缩饼干三年,做梦都想喝一口老婆煮的绿豆汤。去年她走了,我才明白,那汤里根本没放糖,甜的是她的手温。”
再后来,是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跪在地上哭诉:“我是‘未来饮食公司’区域经理……我推广凝胶五年,让我妈也吃……她说难吃,我说科学进步不能守旧……上个月,她脑梗走了,最后一句话是‘想喝你小时候我熬的南瓜粥’……对不起啊妈……”
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说着最平凡、最破碎、最不堪回首却又最珍贵的记忆。每一句话落下,田里的薯苗便轻轻摇曳,仿佛在倾听,在回应,在记录。
到了深夜,月光洒满长桌,忽然所有人的碗中粮食泛起微光。抬头望去,北斗锄星熠熠生辉,七颗星辰连成一线,直指问田中央那株“记名种”。
它开花了。
一朵极小的、乳白色的花,花瓣五裂,散发出难以形容的清香。花蕊深处,缓缓浮现出四个字:
>**“我们回家了。”**
李砚之走到禾生身边,轻声道:“你看,土地从来不是被动承受耕耘的对象。它是活的,是有记忆的,是能爱、能痛、能等待的亲人。”
禾生望着满桌残羹冷炙,望着那些仍在流泪进食的人们,忽然笑了:“所以我一直搞错了。我不是在种红薯,我是在种‘人’。”
十年后。
守问堂已成为“世界耕忆中心”,每年举办“全球忆食节”。各国元首都需提交一份亲手书写的“童年餐桌回忆”方可参会。曾经的敌对势力纷纷转型,推出“记忆认证农产品”,标签上印着真实农户的照片与故事。
而那株“记名种”早已长成参天巨木,树干如盘龙,枝叶覆盖方圆十里,被称为“万姓名木”。它的果实形似谷粒,落地即生,唯有一种人才能采摘??必须先讲述一段自己亲身经历的饥饿或温情。
禾生年过半百,两鬓斑白,仍每日下田。
某个黄昏,他教一个小女孩辨认虫害。女孩仰头问:“禾爷爷,你说土地会说话吗?”
他指着脚下,微笑:“你看不见字,是因为你还太幸福。等哪天你真饿过,就会听见了。”
女孩似懂非懂,却认真点头。
晚风拂过,风铃轻响。
九十九枚银铃,再次齐声吟唱。
而在无人注意的角落,一株新芽悄然破土,叶片背面,静静浮现三个稚嫩墨迹:
>**“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