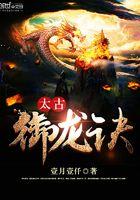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综武:我家娘子是状元 > 第537章 一石二鸟找陆小凤开启二段任务(第1页)
第537章 一石二鸟找陆小凤开启二段任务(第1页)
孔雀山庄创始人高瞻远瞩。
用看似“大家族病”的规矩让后辈学会谨言慎行,用至少需要十三年才能练成的绝学,打磨后代的心性。
最凶厉、最绝妙、杀戮最重的机括暗器孔雀翎,不仅没有妨主,反而成为守护。。。
春风拂过江南,杏花如雪般簌簌飘落,林昭笔尖微顿,一滴露水自花瓣滑落,恰好打在宣纸边缘,晕开一圈淡淡的墨痕。他并不懊恼,反而轻笑一声,顺势将那点晕染勾勒成一只翩跹的蝶影。“你看,天意都来添一笔。”他侧头对沈清璃道。
她正倚着桃枝远眺,闻言转眸一笑:“你总是能把瑕疵说得像恩赐。”
“因为与你有关的一切,本就无瑕。”他执笔补上蝶翼细纹,神情专注,“这一幅,不只是赏花,更是重逢。三年战火,七日生死,十个月康复调养……我们终于走到了这一天。”
沈清璃轻轻抚过画卷边缘,指尖触到尚带湿意的墨迹,心头忽地一颤。她忽然想起那个雨夜??大军被困于玉门关外,敌军围城三重,粮尽箭绝。她率死士夜袭敌营,却被一支淬毒冷箭贯穿右肩。那一瞬,她以为自己会死在荒漠之中,魂归黄沙。可支撑她撑到最后的,不是军令,不是忠义,而是梦里一次次浮现的画面:林昭坐在书院檐下读书,阳光洒在他眉间,风掀动书页,他抬头对她微笑。
“你知道吗?”她低声说,“我在昏迷时,梦见了你。”
林昭抬眼,目光温柔似水。
“你说,‘清璃,回来吧,杏花开了’。”她的声音微微发颤,“那一刻,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原来人真的可以靠一句话活下来。”
林昭放下笔,握住她的手,掌心温热而坚定。“所以我说过,轮到我保护你了。”
“可你从未真正离开过我。”她望着他,“哪怕千里之外,你也一直在等我归来。”
身后弟子们悄然退去,只留二人静立花海之间。远处溪流潺潺,几只白鹭掠过水面,惊起涟漪层层。林昭从怀中取出一枚青玉簪,雕工朴素,却透着温润光泽。“这是我当年在小镇集市上买的。”他说,“原本想等你中状元那天送你,结果拖了八年。如今补上,不算晚吧?”
沈清璃接过玉簪,指尖轻抚其上刻痕??那是两个并列的小字:“昭”与“璃”。她眼眶骤然发热,将玉簪缓缓插入发髻,仿佛完成了一场迟来的仪式。“从此以后,”她轻声道,“无论身处何地,我都带着它。”
归途上,马蹄踏碎落英,春光如酒醉人。回到京城后,林昭着手整理《清璃传》第三卷,题为《破阵录》,记述她亲征西域、连破十二部之壮举。书中不仅详载战事谋略,更收录她在军中所作诗文十余篇,其中一首尤为动人:
>**铁衣寒照月,孤城闭霜烟。**
>**不求封侯印,但护故园田。**
>**血染旌旗赤,风吹鼓角残。**
>**若得天下安,何惜此身捐。**
此诗传出后,民间争相传诵,甚至有乐坊将其谱曲,在茶楼酒肆间低吟浅唱。皇帝听闻,特召太常寺编入雅乐,列为国殇祭礼必奏之章。
然而,平静未久,朝局再生波澜。
某夜,林昭正在灯下校稿,忽闻门外脚步急促。一名黑衣密探跪地呈信:“夫子!边关密报??北狄残部并未彻底瓦解,其王子赫连曜携五千精骑隐匿于瀚海深处,暗中联络吐蕃旧贵族,意图复起。更令人震惊的是,朝中有人通敌,已向其泄露我军布防图!”
林昭眉头紧锁,立即命人封锁消息,并连夜赶赴兵部机要司。然而当他抵达时,却发现沈清璃早已立于舆图之前,一身便服,神色冷峻。她手中握着一封密函,火漆印已被揭开。
“是赵德全。”她声音极轻,却如刀锋划过寒冰,“他在礼部任职三十年,表面守礼崇儒,实则私通外邦,借赈灾之名挪用军饷,资助狄人打造兵器。不仅如此……他还试图策反我麾下副将李元凯。”
林昭心头一震:“李元凯?可是你在白狼川之战提拔的那个年轻人?”
“正是。”沈清璃点头,“他出身寒门,父母死于狄人劫掠,对敌恨之入骨。我以为他是可用之才,却不料其弟被俘多年,近日突获释放,还带回一封家书,言称只要他倒戈,便可保全家性命。”
“人心最难测。”林昭叹息,“但你打算如何处置?”
“明日早朝,我会当众揭发赵德全。”她目光凛然,“至于李元凯……我要见他一面。”
次日清晨,紫宸殿内鸦雀无声。沈清璃出列奏对,条理分明地列出赵德全七项罪状,每一条皆附证据确凿。赵德全起初强辩,直至侍卫搜出其府中密室藏有的狄人虎符与金印,方才面如死灰,伏地认罪。
皇帝震怒,当即下令抄没其家产,贬为庶民,流放岭南。而关于李元凯一事,沈清璃请求暂缓处置,愿亲自前往军营劝诫。
三日后,她独骑赴边,直入李元凯营帐。
帐中烛火摇曳,李元凯跪地不起,双手颤抖:“先生……我对不起您,对不起将士们……但我弟弟他还活着啊!他们说,若我不做内应,就要把他千刀万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