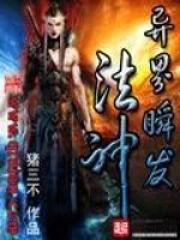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大明第一国舅 > 第643章 一以贯之(第1页)
第643章 一以贯之(第1页)
虽说老丈人来了,不过马寻也只是招待一番,又带着家小进宫了。
这也没什么可担心的,刘伯温和刘?在徐王府依然可以十分自如,没人会亏待他们。
刘姝宁有些好奇,也有些担心,“夫君,为何您执意要让刘。。。
风雪在帐外呼啸,火盆里的炭块噼啪作响,映得允恭佑的脸忽明忽暗。他蜷缩在毛毡上,双手捧着热茶,声音微弱却清晰:“岳父,您可知道,一个王朝的崩塌,往往不是从外开始的。”
马寻凝视着他,目光如刀。他早已察觉这孩子不同寻常??三岁能背《资治通鉴》,五岁解《九章算术》,七岁便敢与李景隆论造船之法。若非亲眼所见,谁会信?可如今,这番话竟出自一个八岁孩童之口,且句句直指天机。
“你说‘紫微星坠’,是哪一年?”马寻低声问。
“万历十年。”允恭佑抬眼,“张居正死后第三日,紫微垣中主星黯淡无光,京师有异象现于夜空,百姓皆言天子失德。实则……那是陨石坠落大气层所致。但自此之后,皇帝深居不出,内阁党争愈烈,东林、浙党、齐党互攻不休,边防废弛,女真悄然崛起……”
马寻听得脊背发凉。他虽不通天文,却知紫微为帝星所在,古来帝王无不重之。若真有此变,必被解读为天命将移。
“那你告诉我这些,不怕改变历史?”马寻盯着他,“你不是说,蝴蝶一振翅,山河皆易色?”
允恭佑苦笑:“可若什么都不做,结局只会更糟。我来此世,并非只为旁观。我是被选中的‘守序者’??一道来自未来的意志,借我之身传递警示。但我不能直接干预,只能引导像您这样的人去行动。”
“所以你是工具?”马寻冷笑。
“也是囚徒。”允恭佑低头,“六百年后,人类已掌握时空观测技术,发现大明若能在十五世纪完成工业化启蒙,则华夏可避近代百年屈辱。于是派出意识投射体,寻找关键节点人物。而您,马寻,是唯一能打破‘封闭锁国?停滞衰亡’循环的人。”
帐内死寂。马寻缓缓起身,走到案前,铺开那幅《寰宇通志图》。他的手指划过南洋航线,停在“新夏”二字之上。
“你说我能扭转乾坤,那我就从这里开始。”他声音低沉,“海外拓殖不止是为了土地和资源,更是为了建立一个不受朝堂掣肘的‘第二中枢’。只要我们在新夏站稳脚跟,哪怕中原倾覆,文明火种犹存!”
允恭佑眼中闪过一丝震惊:“您……已经想到这一步了?”
“你以为我只是个好大喜功的国舅?”马寻回头一笑,“我在军中练兵时便设想过:若朝廷腐朽,边将拥兵自重,百姓流离,我该如何保全社稷血脉?唯有另立根基。就像当年周人避商乱于岐山,秦人守西陲以待天下有变。”
允恭佑猛地站起,激动道:“若您真能建成海外自治政体,再引入未来科技理念,提前发展蒸汽机、电报、铁路……甚至组建现代军队……大明或许真的可以跨越工业革命门槛!”
“慢。”马寻摆手,“一步登天,必遭反噬。我要的是渐进变革。先以垦荒为名,在新夏设立‘工学院’,教授数学、物理、机械;再用海外利润反哺国内军工改革;最后推动科举增设‘格物科’,让天下读书人不再只知四书五经。”
允恭佑连连点头:“对!知识结构决定国家命运。若能让士大夫接受科学思维,意识形态就不会僵化。等到电力、钢铁、轮船成为日常,旧制度自然瓦解。”
马寻忽然压低声音:“但我需要帮手。朝中大臣多迂腐守旧,徐达可用,李景隆尚可教,余宏懂实务……燕王朱棣呢?你觉得他可信吗?”
允恭佑沉默片刻,终是叹道:“他野心极大,手段狠辣,日后必成大患。但他也是最有可能推动军事现代化的人。若您能在他尚未羽翼丰满之时加以引导,或可将其变为改革利器,而非夺权祸首。”
马寻眯起眼睛:“那就让他去管航海学堂。给他权力,也给他规矩。我要让每一艘出海的船,都带回新技术、新思想,而不是仅仅几筐土豆和玉米。”
两人正密谈间,帐外忽传来急促脚步声。亲兵掀帘入内:“将军,斥候回报,鞑靼残部集结于阴山北麓,似欲联合瓦剌共犯大同!另有一支轻骑绕道朔州,疑图偷袭我靖北堡粮道!”
马寻霍然起身,抓起披风:“传令三营即刻集结,骑兵先行截击朔州方向敌军,步兵携火炮随后跟进。再派飞鸽传书至大同守将,令其紧闭城门,不得擅自出战。”
亲兵领命而去。允恭佑颤声道:“岳父,这次战役……历史上没有记载。”
“没有记载?”马寻挑眉。
“说明它本不该发生。”允恭佑脸色苍白,“原本也速迭儿败退后,鞑靼三年内无力南侵。但现在他们反应太快了……有人在背后操纵局势。”
马寻瞳孔一缩:“你是说……另有势力插手?”
“极北之地,曾有神秘部落供奉‘黑曜石碑’,碑文刻着未知文字,据传能窥测天机。六百年后的考古学家称之为‘前文明遗迹’。我怀疑……有人利用类似技术,在暗中干扰历史进程。”
马寻冷笑:“不管他是神是鬼,敢动我大明边疆,就得付出代价。”
次日拂晓,马寻亲率三千龙骧军疾驰朔州。风雪未歇,天地苍茫。行至半途,先锋哨骑急报:前方山谷发现大量马蹄印,深入约十里处设有伏兵迹象。
马寻立马高坡,望远镜扫视四周地形。只见两侧山势陡峭,中间仅容两车并行,确为绝佳伏击地。他嘴角微扬:“果然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