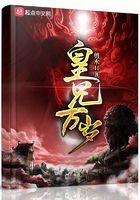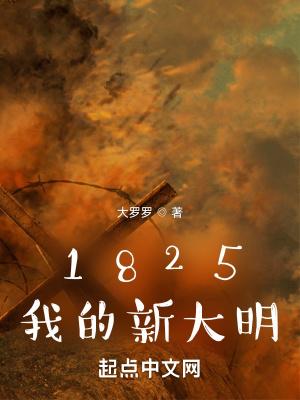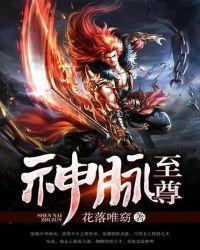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儒道玄途 > 第二百七十六章 郑凌峰归来(第3页)
第二百七十六章 郑凌峰归来(第3页)
>三、凡苦难无人记录,便是第二次杀害。
与此同时,失踪的老者再次现身。
他在云州学堂废墟升起白幡,上书:
>“此处不说正确的话,只说真实的话。”
每日清晨,他坐在塌陷的讲台前,面前摆一只空陶碗。有人来倾诉,他就点头,将话语记在心上;有人愤怒质问“你究竟是谁”,他只答:“一个替别人记住痛苦的人。”
越来越多的人赶来。有被罢官的县令、有流产的接生婆、有因揭露漕运黑幕而全家遭难的账房先生……他们围坐废墟,轮流讲述自己的故事。老者从不打断,也不评判,只是偶尔举起竹杖,在空中轻轻一点,仿佛为某个词加注标点。
第七日,天空阴沉,乌云压顶。
一位年轻僧人徒步而来,袈裟破烂,脸上带伤。他跪倒在老者面前,声音颤抖:“大师,我来自五台山清凉寺……我们寺收藏了三百年的《贞观遗诏》原本,记载太宗晚年悔恨杀伐过重,欲废死刑,推行‘赎刑制’……可这份诏书一直被历代帝王封锁,从未公布!我师父临终前让我带出来,可刚到山下就被追杀……二十一名师兄弟,只剩我一人逃出……”
他从怀中掏出一块焦黑的绢布,上面字迹残缺,但依稀可见:
>“朕统六军,平四方,然血流漂杵,夜夜闻冤魂哭……若后世仍有以‘法’为刃、不察民情者,非吾子孙也。”
老者接过,凝视良久,忽然仰天大笑,笑声中竟含悲怆。
“你们知道为什么苏蘅要死吗?”他环视众人,“因为她写出的每一个字,都在打碎一个谎言。而掌权者最怕的,从来不是叛乱,是真相。”
他站起身,将绢布投入火中。火焰腾起,竟呈青蓝色,映照出一座虚幻宫殿的轮廓??正是当年沉入意海的信狱殿!殿门微启,一道身影缓步走出,白衣飘渺,眉目温润,正是苏蘅。
但她并非实体,而是由万千声音凝聚而成:渔女的歌谣、寡妇的哭诉、学子的朗读、老农的叹息……所有曾因《人间录》而发声的人,他们的声音汇成了她的形。
“我未走。”她说,“我只是变成了你们共同的记忆。”
众人伏地叩首,泪如雨下。
老者却转身面向东方,低声说:“接下来,轮到你们写了。”
半月后,新版《人间录》正式发行,新增“帝王篇”“僧道篇”“外邦篇”,全面审视权力源头。与此同时,民间自发成立“问心盟”,誓言每十年修订一次《人间录》,确保其始终反映时代之痛。
而那位麻衣老者,又一次消失不见。
有人说他在北方边境教牧童识字,有人见他在西南深山帮苗人立约自治,还有樵夫称曾在峨眉金顶看见他与一头白鹿并立,手中竹简随风化蝶,飞向云海。
十年又十年。
当第一个通过“巾帼科”成为宰相的女子主持朝会时,她特意在殿中悬挂一幅字,是当年望心亭少年记下的那句:
>**“己可正,世若不公,何以正之?唯有问。”**
她每天上朝前都要默念一遍。
而在遥远的西域,龟兹古城新建了一座无名碑,碑上不刻文字,只有一支深深的刻痕,像是有人曾用尽一生力气写下一句话,却又被风沙抹去。
唯有夜深人静时,若有诚心之人俯耳贴近碑面,会听见细微的声响??
那是千万人的低语,汇聚成一句永恒的追问:
>“你说的,是真的吗?”
风吹万里,铃响不绝。
那条永远走不完的路,依旧有人在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