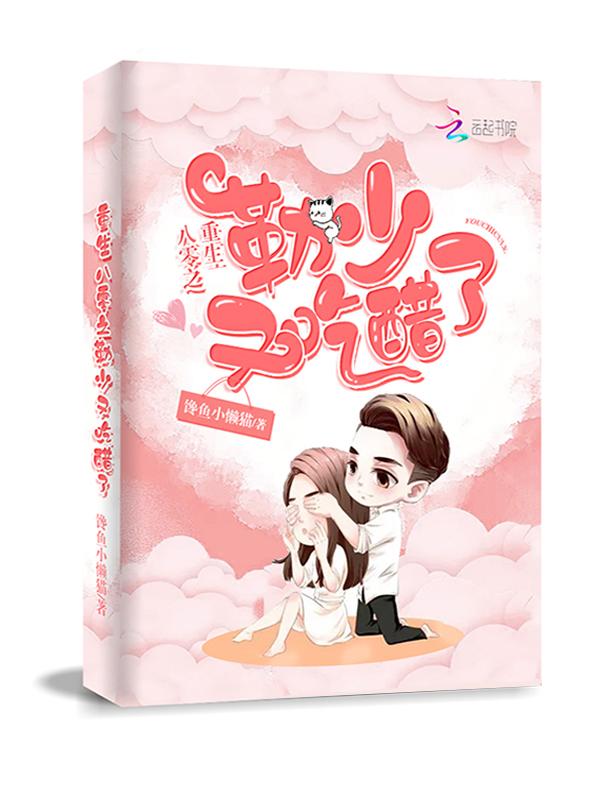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要宅斗不要武斗啊! > 不要害怕(第4页)
不要害怕(第4页)
她不知道。
为女子,当静姝柔顺,父母所言,莫不顺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她这条性命本就来自于父亲,又受父亲多年养育之恩,才堪堪活到今日。
子女天然是亏欠父母的,她全该听从父亲安排。她忤逆父母、不愿换嫁,已是不孝。
父亲曾说,天下多的是流民百姓衣不果腹,她作为他的女儿出生,自小锦衣玉食,仆从环绕,不知有多少人羡慕这样的日子。
嫁给那样的人,继续她锦衣玉食的日子,不过伺候好丈夫,做好为人妻子的本分,便比不知多少艰难挣扎着才能果腹的百姓强了。
她本该知足。
可她不愿再过这样的日子了。
她活了十四年,日日谨小慎微,受尽冷眼。即使无数次欺骗自己,也非常清楚未曾有人真心疼爱过她。
这样的日子,也许有很多人羡慕,但她一日也不想再过了。
于行宛也不知该恨谁。
恨父亲,父亲好似并不欠自己的,她已享了天大的恩情,莫非还要拼死反抗、扰得家中不得清净,恩将仇报吗?
恨那染了花柳的王煜,二人面都没见过,便草草定了她的终身。这场差点逼死她的婚约,不过一场交易,父亲要利益、要官场升迁,他们要体面、要柔顺安静的新妇。
或许谁都该恨,谁都不该恨。
于行宛无法抉择,只好恨自己,只好一死了之,偿还父亲所给的性命。从此谁也不欠,也再不必如此度日了。
可上天派下恩德,不仅教她没死成,还阴差阳错同另一人有了交集。
她默默无闻的十四年里,从未有人肯认真同她讲话、听她讲话。她一日日地盼望,期待未来为人妻子,会有丈夫与自己同心,她再不必如此孤单。
恳切盼望的时候,一切都落空了。
反倒是停止期待,决心结束这一切的时候,偏偏有人同她一起跳下河来。
她脑中乱糟糟的,对奚燃所问,不知如何作答,只连番说:“不知道,我不知道。”
这时,听到奚燃唤她:“于行宛。”
她下意识应声。
他像是很犹豫的样子,斟酌着用词,不知道该怎么说,她鲜少见他有这样的时候。即使只相处了短暂的时间,她也总是见他不管不顾、直言不讳,从没有如此情形。
她忘却了之前纠结的一切,只专注地盯着他,想知道他要说什么。
她听到他说,她听到他说——
“于行宛,你不要再跳一次河了,河水好冷。”
“你。。。。。。不像客栈掌柜,你不聪明、不厉害,不能打得过家人,不能应付事后场面。可是,你不要害怕。”
“现在,你就是我,而我是你。”
“你不知道怎么做,那就由我来替你做。”
她听到他说,“我来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