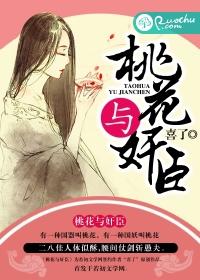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装傻三年:从状元郎到异姓王 > 第六百三十六章 为了王庭(第1页)
第六百三十六章 为了王庭(第1页)
“这不就来了。”沈浩满脸带着忍不住的笑意。
“哈哈哈哈。”李峰此时的笑声中充满畅快。
总算是让他们等到破局的时机了。
然后几人便开始商议接下来的计划。
他们可以执行计划。
但也要有后续的计划。
比如沈浩就对后续西域会不会出手这件事上给出了一些提议,并让人先行去准备。
一天后。
随着斥候一条条的消息送回来。
众人的计划不断完善。
而沈浩和李峰才知道这次巴特尔的确是大动作。
他们竟然在秘密运兵道集结了三万大军。
同时。。。。。。
少年吹出那一声短音之后,便又闭上了眼睛,仿佛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晨光斜照在他瘦削的脸颊上,映出一层近乎透明的苍白。他的呼吸微弱,胸口起伏如风中残烛,唯有那支陶笛仍紧紧贴在唇边,像是从不曾离开过。
哨兵怔在原地,铜钟余音未歇,在耳膜深处嗡鸣不止。他下意识后退半步,手按刀柄,却迟迟不敢拔出。整座城楼陷入一种奇异的寂静??不是无声,而是声音太多,多到让人无法分辨哪一个是真实,哪一个是幻觉。风掠过旗幡,竟带出《萤火虫》的尾调;守夜人昨夜遗落的竹梆子自行轻响,三长两短,正是心灯院警讯暗语;就连城墙砖缝里一株枯草,也在微颤中发出极细的呜咽,像极了母亲哄睡时哼唱的小调。
“你……是谁?”哨兵终于开口,声音干涩得如同砂纸摩擦。
少年没有回答,只是缓缓睁开眼。那是一双极清澈的眼睛,黑得不见底,却又亮得能映出整个天空。他望着哨兵,嘴角再次扬起一抹笑,轻得几乎看不见。
“我叫阿念。”他说,嗓音沙哑,却带着某种奇异的韵律,“我走了很远。”
“从哪儿来?”
“从有歌声的地方。”他坐起身,将陶笛小心地揣进怀里,动作轻柔得像在安放一个婴儿。“你也听到了吧?刚才那一声。”
哨兵点头,喉咙发紧:“它……不该响的。钟没人敲,怎么会自己响?”
“因为它记得。”阿念仰头看向东方初升的太阳,“每一口钟、每一片瓦、每一粒沙,只要曾经听过歌,就永远不会真正沉默。它们只是在等一个人,轻轻推一下门。”
他站起身,摇晃了一下,扶住墙才没跌倒。哨兵本能想伸手扶他,却被那股无形的气场所阻??少年周身似乎笼罩着一层看不见的波纹,空气因之微微扭曲,仿佛他每走一步,都在拨动一根极细的弦。
“你要去哪儿?”哨兵问。
“去下一个听见她的人那里。”阿念抬头望向远方,目光穿透群山与云霭,“她一直在找能听见她的人。而我能带他们相遇。”
话音未落,远处传来急促马蹄声。一队巡骑自官道疾驰而来,为首者手持令牌,高呼:“边关重地,闲杂人等速速回避!”哨兵连忙将阿念拉至墙角遮蔽处,低声道:“别出声,这是巡查司的人,专查流民异言。”
马队奔近,领头校尉目光锐利扫视四周,忽而勒马停住,鼻翼微动:“刚才……有没有听到钟响?”
无人应答。
“不可能!”校尉翻身下马,快步登上城楼,亲自查验铜钟。他伸手触摸钟体,指尖触到一丝温热,皱眉沉思片刻,忽然喝令:“搜!方圆十里内所有乐器一律收缴,凡持笛箫琴瑟者,押送刑部审问!陛下昨夜再颁诏令:‘七音乱政,当绝其根’!”
士兵轰然领命,分头行动。阿念缩在阴影里,脸色愈发苍白。他低头摸了摸怀中的陶笛,指节泛白。
“他们怕声音。”他喃喃道,“怕心会醒。”
哨兵听得心头一震,正欲追问,忽觉脚下一震。紧接着,地面传来低沉的搏动,由远及近,如同巨兽的心跳。城墙根下的碎石无风自动,排列成一圈圈同心圆纹。更诡异的是,那些被下令收缴的民间乐器??藏在百姓床底的琵琶、供奉在祠堂的编钟、孩童手中破旧的泥哨??在同一时刻齐齐震颤,发出细微共鸣。
阿念闭上眼,嘴唇微动,似在回应某种频率。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东海渔村,那个曾孕育阿澈的海边小屋,屋顶瓦片突然掀开一角。一道银光自屋内冲天而起,竟是那片干枯的桂花叶化作飞蝶,振翅北去。而在西域沙漠深处,独眼老者跪于“启明”玉笛前,泪流满面,口中反复呢喃:“第七代已动,第八代将启……母巢的锁链,终究断了。”
心灯院旧址,那支留在祭坛上的“归音”玉笛,此刻悄然离地三寸,缓缓旋转。一道细若游丝的光脉自笛身延伸而出,贯穿大地,直指边关方向。仿佛有一条看不见的线,正在将散落四方的音种者逐一串联。
阿念猛然睁开眼,瞳孔中闪过一道蓝光。
“他们开始清剿了。”他对哨兵说,“但这恰恰说明,她们快醒了。”
“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