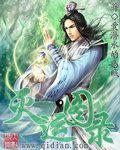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装傻三年:从状元郎到异姓王 > 第六百三十九章 气晕的巴特尔(第1页)
第六百三十九章 气晕的巴特尔(第1页)
“死了,都死了,天罚,是天罚。”
斥候的声音里全都是颤抖和恐惧。
“啪!”
一旁巴图鲁见状一巴掌抽在癔症的斥候脸上。
这一巴掌的疼痛,使得这名斥候眼神中逐渐多出一抹清醒。
直到这一刻,他才知道自己不知何时已经回到大营。
而他面前,还站着少族长和巴图鲁将军。
他吓得当即惊慌失措道:“少族长饶命,少族长饶命,属下是太害怕了。”
“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运兵道方向会发生巨响。”
巴特尔再次问出着急想知道的问题。。。。。。
桂源的春来得格外早。残雪未消,山脚下的溪流已开始叮咚作响,像是被谁悄悄拨动了琴弦。那棵双色桂树在晨雾中静静伫立,金黄与幽蓝的花瓣随风飘落,落入泥土,也落入过往行人的衣襟。孩子们依旧年复一年地来到这里,捧着残破的乐器,或只是拍手、跺脚、哼唱。他们不懂什么是音律,也不知曾有一人用生命换来了这自由发声的权利,但他们知道??这样“说话”,心里很暖。
而在千里之外的京城,宫墙之内,一场无声的风暴正在酝酿。
太子萧景珩站在御书房外,望着檐角垂下的铜铃。那铃本是禁声令时期的产物,一旦有人高声言语,便会震动示警。如今铃铛早已锈蚀,可它仍悬在那里,像一根刺,扎在新秩序的咽喉上。
“父皇昨夜又没睡。”他低声对身旁内侍道,“还是那些笑声?”
内侍低头:“回殿下,不止笑声……还有哭声、说话声,杂乱无章。太医说,陛下耳中所闻,并非实音,而是心魔作祟。”
萧景珩闭了闭眼。他知道,那不是心魔,是记忆的回响。皇帝一生镇压音乐、铲除乐师、焚毁典籍,甚至亲手将亲妹妹打入冷宫,只因她曾在月下弹了一曲《归雁》。可如今,当千万人的心声借由母巢余波苏醒,那些被刻意遗忘的声音,便如潮水般涌回他的脑海。
“传旨下去,”他终于开口,“拆了这铃。”
内侍一震:“殿下,这是先祖定下的规矩……”
“规矩?”萧景珩冷笑一声,“一个靠恐惧维持三百年的规矩,配叫‘祖制’吗?”
他转身步入殿内,手中捧着一卷泛黄的手稿??那是从废墟中找到的《大周乐志》残篇,记载着曾经辉煌的宫廷雅乐。他曾偷偷命人将其译解,请民间老乐工试奏。第一声响起时,连他自己都怔住了:原来这天下,竟有过如此温柔的声音。
与此同时,南方小镇的茶馆里,柳婆正轻轻拨动琵琶最后一根完好的弦。她的手指早已不灵活,音准也常偏,可听的人却越来越多。不只是本地村民,甚至有从北方远道而来的旅人,带着断笛残鼓,只为听她弹一段不成调的曲子。
“您总说‘阿念’,”一日,有个少年忍不住问,“他是谁?真的存在过吗?”
柳婆停下动作,抬眼望向窗外。阳光斜照进来,落在她布满皱纹的脸颊上,映出一丝极淡的笑意。
“你说风有没有形状?”她反问。
少年愣住。
“你看不见它,但它吹过麦田时,你会听见沙沙声;它掠过屋檐时,会带起铃响;它穿过竹林,就像有人在低语。”她缓缓道,“阿念就是这样的风。你不记得他的模样,可你每次开口唱歌,那就是他在呼吸。”
少年沉默良久,忽然起身,走到角落拿起一把蒙尘的陶埙,笨拙地吹了起来。不成调,却真诚。其他客人也陆续加入,有人敲碗,有人拍桌,有人轻声哼唱。一时间,小小茶馆竟似成了最古老的祭坛,供奉着失落已久的神明??**声音本身**。
柳婆闭目聆听,眼角滑下一滴泪。
而在西北边陲,一座废弃的烽火台下,一名老兵跪坐在沙地上,面前摆着半截断裂的号角。那是他年轻时随军出征所用,后来被收缴销毁。他侥幸藏下这一段,三十年未曾触碰。昨夜,他梦见自己站在战场上,耳边不再是战鼓与嘶吼,而是一首陌生的歌。醒来后,他鬼使神差地翻出了这角。
他颤抖着将它凑近唇边。
一声呜咽般的长鸣划破荒原。
刹那间,远处沙丘微微震动,一道微弱的蓝光自地下浮现??竟是第十一座传音枢机的残骸,在感应到共鸣后短暂复苏。光脉如蛛网蔓延,勾勒出一首古老旋律的轮廓:《舍》的第二段。
老兵怔住,老泪纵横。
“原来……我们一直都在被听着啊。”
他不知道的是,这一刻,远在东海之滨的一艘渔船上,一个小女孩正趴在船头,对着海浪哼歌。她母亲惊恐地捂住她的嘴:“别唱!以前唱的人都被抓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