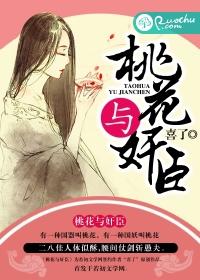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浓浓 > 7075(第8页)
7075(第8页)
方才从那盏茶中汲取的气力已渐耗尽,兰浓浓亦恐久留露了形迹,说罢便撑椅缓缓起身。然双足已冻得麻木,身形摇晃,看得人不由蹙眉。
对此,她自有应对,身子朝旁侧云明姑姑一倚,亲昵笑道:“我脚麻了,劳云明姑姑扶我一程。走几步活动开便好了。”
几人未再多言,一路护着她行至院门。那府中婢女见状忙疾步迎上,小心翼翼地将人搀稳。马车早已候在一旁,踏凳亦已摆好,有婢女静立候着,只待她登车。
兰浓浓未留意众人并未踏出院门。她亦不愿给姑姑们平添烦扰,借着碧玉二人的搀扶,佯作已无恙,站直身子朝院内挥手,眸弯如月,笑靥明快,
“外头天寒,姑姑们快关门回去。莫与我争,我待你们进去了再上车。”
该交代的既已交代,几人便不与她争执,纷纷颔首后掩上院门。
红木门方合拢,兰浓浓身子倏然软下,惊得二婢顿然色变,却被她眼风止住不敢出声。碧玉低声道了句“得罪”,便俯身由青萝将人负至背上,步履轻捷地登车。
兰浓浓措手不及,待眼前晃影定住,人已卧于马车软榻。她未多问,只朝碧玉投去一瞥,便收回目光——
马车直入府中,停于寝院门前。
兰浓浓不知何时睡去,直至察觉被人触碰,方蓦然惊醒。碧玉见状急退请罪:“夫人容禀,奴婢见您今日劳累,不忍唤醒,便自作主张欲抱您下车,绝非有意冒犯。”
见是她,兰浓浓心下虽余悸未平,更多却是松缓,遂摆手令其起身,自行撑臂坐起下车。
府中的琉璃暖罩早已架起,室内温暖如春,无需再披斗篷。下车时无意抬头,见日头虽在正中,却被阴云半遮,天色一片阴沉。
回到房中,暖意更重,围脖及高领的袄裙逐一褪下。兰浓浓走至等人高的雕花鎏金镜前,偏过头端详,颈间肌肤上痕迹大多已变淡,却仍有几处青紫未消,瞧着触目惊心。
午膳是独自用的,皆是清淡菜肴。她强撑倦意等了片刻,待汤药饮尽,便转入寝卧,上榻沉沉睡去——
午后未时,天又飘雪。
覃景尧偏首望向窗外,只见大雪如破了天幕般连绵砸落。他忍了又忍,终是霍然起身,将满案公文与一众下官的恭送声尽数抛在身后。
“夫人可用过膳了?进了多少?药可喝了?”他一面疾步向外,一面沉声问道。
同泽忙为他系上披风,撑起墨色油伞,紧随其后回话:“回大人,府中尚未有消息传来。据先前下人禀报,夫人午时初便已回府,此刻应已用膳服药。”
覃景尧未再开口,也知此刻问不出更多。只是心中那股想见她的念头骤然汹涌。
立刻便要见到她,一刻也等不得。
他端坐马车中,身姿如大马金刀,腰背挺拔,双目紧闭,面色平静,然心下却一片纷乱。
她未见着那些人时,分明急切难安,可见了面,却那般冷静自持,未抱着人嚎啕痛哭,言谈间条理清晰,便是回程途中,亦未露半分隐忍。
如今回到府中,更是若无其事——
心头一股无名烦躁涌起,气息骤然沉浊。覃景尧猛地睁眼,眉峰紧锁。大雪纷飞,车马难行,速度比平日慢了一倍有余。
他再难忍耐,霍然起身跃出车厢,命人卸下车驾,翻身策马,一声沉喝便冲破漫天飞雪疾驰而去。
府门檐下的护院远远望见一人单骑踏雪而来,急忙挥手洞开朱门。炙热的喘息与乘隙灌入的寒气于空中相撞,在黑曜石地面上凝下一行蜿蜒水迹。
马蹄踏过,府门轰然合拢,溅起的水珠瞬间绽作朵朵冰花。
覃景尧甩开缰绳,解下披风,大步流星直奔后院。往日一步一景的亭台游廊,此刻却显得格外漫长,漫长到让他恨不得挥手尽数夷平,好教他一入府便能直抵她的院落,一步便能跨到她的眼前。
他沿着主路直行,逢廊穿廊,遇园破园,近两刻钟的路径,竟被他硬生生压缩至一刻钟。
将亭与同泽虽皆是俊拔亲卫,却仍不及大人伟岸,此刻追赶的步伐几乎与奔跑无异。待终于赶到夫人院外,前方疾行的身影骤然定住。
将亭心神一凛,暗舒长气,立即挥手命毗邻院落的下人速将常备的暖炉熏服送来,他绕至大人身前,手法利落地褪下那身浸透寒气的官袍及中衣。
恰时常服送至,接过后迅捷更换妥当。与此同时,小厮已用特制的细长暖炉将墨发熏暖。全程不过几次呼吸之间,待覃景尧提步入院时,周身已不带半分寒意。
将亭暗自舒气,遣退众人,正欲寻郭管家交代事宜后再回来候命。行至中庭,恰遇顶着满头风雪狂奔而归的同泽。二人目光相撞,彼此打量,均是不约而同地挑眉。
对比同泽一身狼狈的冰霜,仅是气息微乱的将亭忍不住挺直腰背,脸上掠过一丝得意。
说来二人当年同被买入府中,编入一队习武受训,又同时被大人亲点位至身侧。论能力武艺不相上下,性情更是投契,堪称形影不离,本该是挚友无疑。
在大人代天子巡阅边军之前,也确实如此。往日大人外出,二人向来是一人随行一人留守,轮番更替。
只此次大人离京日久,临行前二人皆向大人自荐随行,甚至当着大人的面交手比试。最终同泽略胜半招,争得随行之机,将亭则被留在京中看守。
留守之责虽重,非心腹不能担当,然于他们这等近卫而言,纵被委以重任,也远不及随侍大人身侧来得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