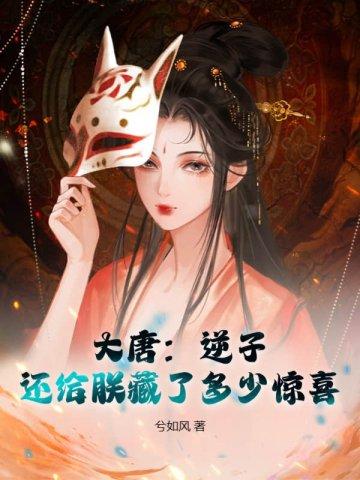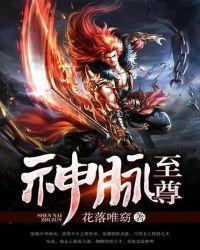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民俗从傩戏班子开始 > 第199章天门22(第3页)
第199章天门22(第3页)
小满蹲下身,抓起一把泥土,轻轻撒在一朵蓝花周围。“闭上眼睛,想想你们最怕黑的时候,是谁给你们讲故事?想想你们第一次学会写字,是谁握着你们的手?”
孩子们照做。
片刻后,风起了。
花瓣飘舞中,空气中浮现出模糊影像: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坐在教室里,用方言朗读课文;他在雨夜里打着伞送孩子回家;他把自己的饭让给饿肚子的学生……
“我记得你!”一个小女孩突然喊道,“你教过我写‘希望’两个字!你说,只要笔画不歪,心就不会迷路!”
影像颤动了一下,随即清晰起来。
男人转过头,笑了。
“谢谢你们还记得我。”他说,“我可以回家了吗?”
小满点点头,牵起他的“影子”,轻轻放在村口那块石碑上。刹那间,原本空白的碑面浮现出三个字:
**周文昭**
村民们闻讯赶来,老人们抹着眼泪说:“是他啊……我们都快忘了……”
当晚,全村点亮灯笼,跳起傩舞。没有专业演员,没有剧本,每个人随心而动,动作却惊人地一致,仿佛某种古老仪式正在自动复苏。
而在昆仑学院旧址,一座新的建筑悄然成型。它没有钢筋水泥,而是由亿万朵蓝花编织而成,形似一朵倒悬的莲花,根系深入地脉,花蕊中悬浮着一面巨大的铜镜。镜面不再映照人脸,而是滚动显示着全球最新被“唤醒”的名字。
这里被称为“忆归堂”。
任何人只要携带亲人的遗物或记忆片段前来,便有机会通过共感共振,与逝者建立短暂连接。
一位母亲带来了女儿的红领巾,她在镜前低声诉说思念,三分钟后,镜中浮现出女孩的身影,笑着说:“妈,我在那边很好,有很多朋友一起上学。你要按时吃饭。”
一名战士捧着战友的军牌,在镜前敬礼。片刻后,镜中走出一个模糊身影,同样抬手还礼,嘴唇无声开合。旁边的孩子们自发组成合唱团,将他的口型翻译成歌声:
>“兄弟,别停步,
>山河记得我,
>若有风经过你的肩头,
>那是我轻轻拍你说:‘走好。’”
最令人动容的一幕发生在某所孤儿院。
十几个孩子围坐一圈,手中捧着从各地收集来的“无主陶片”??那些曾属于失踪者、却被系统注销身份的人留下的唯一信物。
他们齐声唱起《赎》的最后一段:
>“你不曾离去,只是藏进风里,
>等一句名字,等一场记忆,
>等一个孩子,为你提灯寻你……”
歌声落下的瞬间,所有陶片同时发光,裂开细缝,从中飘出缕缕青烟,凝聚成人形轮廓。他们没有五官,却能让每个孩子脱口喊出他们的称呼:“爸爸!”“奶奶!”“哥哥!”
这一夜,地球上新增了三千二百一十七个“被记住的名字”。
每一个,都是对遗忘协议的宣战书。
而在宇宙深处,CM-7残核仍在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