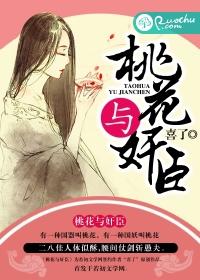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妄窥春山(双重生) > 第60章 瑞雪完结(第3页)
第60章 瑞雪完结(第3页)
今天早晨徐闻听才风尘仆仆从岭南赶回京。
他谁也没见,没有回国公府,也没有去找孟茴和徐季柏,独自在驿站沐浴后,便带着从岭南带的礼,去了新孟府,交与门房,进席落座。
京中稍有地位的都来了,却谁也没有多交谈,只低低的窃窃私语。
东房。
孟茴沐浴更衣,孟祈帮她换上襦裙。
很合身。
孟祈轻叹:“还是瘦了一些,尺寸比以前少不少。”
“没关系啦阿姐,过段时间就养回来啦。”孟茴这么说着,外面已传来了乐声。
“午时了。”孟祈望了一眼,收回视线,再替孟茴一理衣襟后,笑着伸出手,“牵着阿姐。”
孟茴抿着唇,啪嗒握上她的手,随着她的步子一并出了门。
“阿姐,最近姐夫在帮你看铺子嘛?”
“嗯,他人高马大的,几个眼红的邻里都不敢做什么。”
冬月末的天已经很凉的。
襦裙里被细致缝上一层薄薄的鹅绒,叫孟茴一点凉意都觉察不到。
她弯着眼眼笑笑,随着孟祈一步步走近礼场。
远远的,她望见徐季柏坐在次首座的位置,清浅地含着笑望着她。
前世今生的徐季柏恍然一交。
孟茴突然发现,其实前世坐在她及笄礼的徐季柏,也是这样的眼神,藏在表面不高兴之外的专注。
孟茴紧了紧孟祈的手。
真好。
阿姐好好的,阿娘好好的。
她和徐季柏也好好的。
……
孟祈只能送到这个地方。
毕竟是女子成人总要自己走一段,昭示成人行径有德。
孟茴拎着襦裙,走上高台。
她并未束发,如墨一般的发长长铺下,衬得眉眼更翠、更灵。
徐季柏想,孟茴就像一份难能得礼物,活不像人间自然生的,落进了他的怀里。
以前他觉得徐闻听命好,亲人友人爱人都圆满,如今一看,命好的是他。
孟茴拎裙跪坐蒲团,一瞬不眨地望着徐季柏。
徐季柏温笑着起身。
他从托盘中拿过梳子,走到孟茴身后,执起一绺发一梳至尾:“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介尔景福。*”
他声音沉稳,传至礼场每一个角落。
“伤风败俗。”有个人忍不住得说,“要和侄子的未婚妻成亲,还给人行及笄礼!世风日下,难以忍受日后我大胤就要同这样的人统领吗?”
“就是啊,这样不光彩的事,还不遮掩一些,枉我以前还叫他一句徐三爷。”
几人嘀嘀咕咕说着,也不敢大声被人听见。
“有什么不光彩的。”
一道男声骤然响起,传至几人耳中,他们惊愕往后一瞧,赫然见这人竟是他们话中的那位“侄子”。
只是这位小公爷黑了不少,眼睛越发锐利,倒少了以前风流的二世祖模样。
只听徐闻听继而道:“我与孟茴并未定亲,不过是长辈玩笑,她与徐季柏在一起怎么是伤风败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