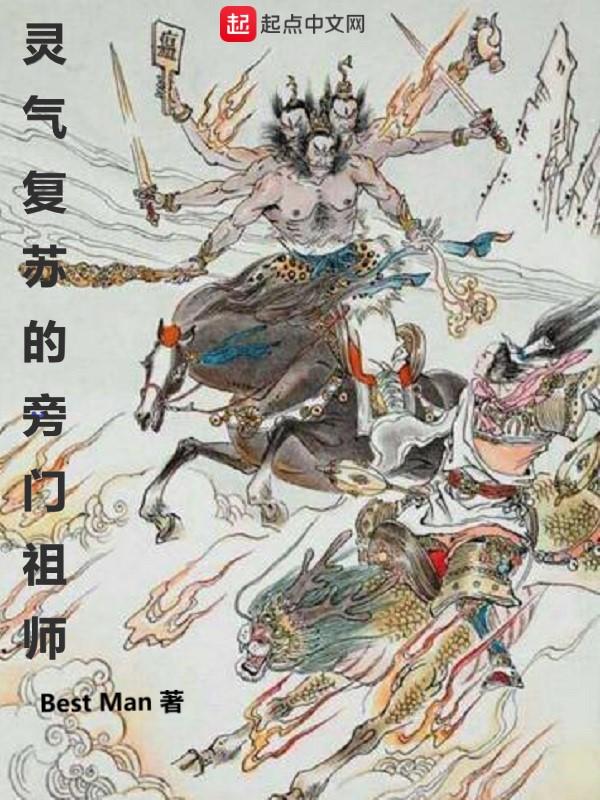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臣心匪石 > 江南道18(第1页)
江南道18(第1页)
云初见那句掷地有声的诘问,如同投入滚油中的星火,瞬间点燃了人群中被压抑的怒火与不甘。
然而,蒋同那番悲悯伪善的福田论,却又像一盆粘稠冰冷的泥浆,兜头浇了下来,让那刚燃起的火星瞬间变得窒息而迷茫。
短暂的死寂中,一种诡异而沉重的气氛笼罩着灯火通明的庙会广场。
就在这时。
“你……你胡说!”
一声夹杂着恐惧,绝望和崩溃的嘶哑哭嚎猛地响起。
人堆里,那个不久前才被云初见指出来、枯瘦得如同冬日残柳的老汉,此刻像被逼到悬崖边的老兽。
他浑浊的老眼泪水涟涟,稀疏花白的胡子剧烈颤抖,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因激烈的情绪而扭曲。
他竟然踉踉跄跄地冲出几步,伸出一双枯枝般、布满冻疮和泥垢的手,用尽了全身残存的力气,死死抓住了云初见的手臂。
那力道大得惊人,像溺水者攥住最后一根稻草。
“你……你懂啥啊!”老汉的声音嘶哑破碎,带着哭腔和一种近乎癫狂的恐惧。
“俺…俺家老大去当了兵!说是报效朝廷,结果……结果人没回来,就……就剩下一把骨头啊!”
他大口喘着气,胸脯剧烈起伏,浑浊的泪水沿着沟壑纵横的脸颊滚落,滴在云初见的衣袖上。
“俺们爷仨……不,就剩俺带着个哑巴儿媳和小孙孙了!田里的粮……交了税,再去掉口粮……一年到头连个……连个给孙儿扯块新布的闲钱都没啊!”
他死死攥着云初见的手臂,如同攥着自己的命,干枯的手指关节泛白。
“三两银子!那是天老爷要命的钱!俺也知道!”
“可……可佛祖是俺们唯一的念想了啊!去年发大水……隔壁村子都泡成了龙王爷的水晶宫!”
“就俺们村……就俺们村……磕了头捐了家里最后一只下蛋的老母鸡供了菩萨的……逃过了劫啊!”他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瞪着云初见模糊的面容,声音拔高,充满了惊恐的控诉。
“就因为你!就因为你刚刚冲撞了菩萨!冲撞了蒋大人!”
“以后……以后再闹灾……谁……谁还管俺们啊?!你给俺们粮食?!你给俺们挡洪水?!你能让俺孙儿不病死吗?!”
他也不知道哪里涌上来的绝望蛮力,猛地用力一推搡。
“快走吧!求你别挡着菩萨的路!别挡俺们活路哇!”这带着哭腔的、绝望的、同时也是最沉重的反戈一击,让云初见猝不及防地被推得一个趔趄。
老汉本就站立不稳,用力过猛之下自己也是一个趔趄,差点摔倒。
这一推,如同推倒了一座无形的壁垒。
“对!老人家说得对啊!”
“敬佛的事哪能让你这种人来搅和!”
“快走快走!求菩萨要紧!”
“灾祸来了就怪你!”
“把他轰走啊!别坏了俺们福田!”
如同溺水的人抓住漂浮物就当成救生船,周围那些原本畏缩挣扎的可怜人,那些刚还在为三两银子愁苦的面孔,此刻在生存本能的驱使和对灾祸重现的强烈恐惧下,仿佛被老汉的恐惧同化了。
他们也躁动起来,几双沾满泥巴、带着同样生活印记的粗糙的手,带着一种麻木而焦躁的齐心协力,七手八脚地推搡着那个身姿挺拔却突然变得有些碍事的青衣人。
力道不大,更多是驱赶的混乱和一种群体宣泄的怪异认同感。
但那瞬间涌来的、带着土腥气、汗臭味和同样深重苦难烙印的敌意与排斥,却像冰冷的毒虫,骤然扑在云初见身上。
几个原本畏畏缩缩、面有菜色的百姓,在绝望和对灾祸的恐惧驱使下,仿佛找到了一个共同宣泄恐惧和怨恨的对象,竟也涌了上来。
那份瞬间涌来的、带着土腥汗臭和被生活碾压到扭曲的敌意,却像冰冷的潮水,猝不及防地拍打在云初见身上。
他微微低头,隔着朦胧的白纱看着那些推搡在他衣衫上,手臂上的手,看着那些在灯火下显得麻木又焦躁的面孔。
心中,确实微微一懵。
不是惊愕于这些手的力量,而是那刹那间的错位。
就在片刻之前,正是这些人因那三两银子而面露菜色,低声咒骂,敢怒不敢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