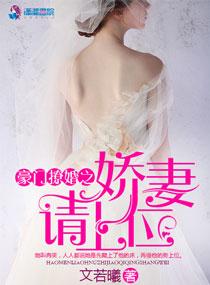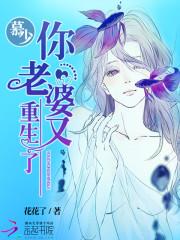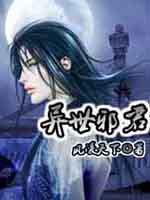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晋末芳华 > 第四百七十五章 伤情感怀(第2页)
第四百七十五章 伤情感怀(第2页)
那一晚,千里之外的建康城居民纷纷惊醒。许多人声称梦见自己站在一口井边,听见井底传来千万人齐声低语:“我不信。”
更有边境守军报告,北地胡营中的战马集体躁动,不肯进食,只对着南方嘶鸣。单于亲自查验,发现马厩地面竟浮现出细密裂纹,形状酷似波形图。
十年后的春天,一个名叫“声墟学派”的团体悄然兴起。
他们不信文字,不信权威记录,只信“错听记忆”。他们行走乡野,收集老人梦话、病者谵语、疯人狂言,认为这些才是被压抑历史的真实回响。他们提出“十重真相论”:同一事件必须有至少十个相互矛盾的说法并存,才算接近真实。
朝廷震怒,下令取缔。可每当查封一处“声墟讲堂”,次日街头便会出现更多涂鸦:“你说的是真的吗?”、“我听到的不一样。”、“也许我们都错了,但这没关系。”
甚至连皇宫内部也开始出现裂痕。
某夜,太子独自读书,忽闻窗外有女子轻唱。歌词荒诞不经,讲述一位皇帝如何被自己的影子取代,从此只会说别人想听的话。太子细听之下,竟发现此曲旋律与宫中每日晨钟暗合,只是节奏偏移了七分之一拍。
他彻夜难眠,次日私访民间,扮作书生,混入学堂旁听。先生正在讲解《晋史?安神纪》,讲到“万民一心,同听共感”时,一名学生举手问道:“老师,如果所有人都听见一样的东西,那是不是说明,其实没人真的在听?”
全堂哗然。
太子悄然离席,回到东宫,写下一生唯一一首诗:
>耳中有铁网,
>心内无回声。
>若问真言语,
>可敢听不成?
此诗未曾刊行,却被一名宫女抄录,藏于绣鞋夹层,带出宫门。数月后,江南各地开始流传一种新游戏:两人对坐,轮流说一句话,对方必须回答“我觉得不太对”。说得越荒谬,越受推崇。孩童以此为乐,情侣借此调情,政客甚至在朝会上公然使用此句反驳同僚。
而在这片日益喧嚣的土地上,仍有少数人选择彻底沉默。
他们被称为“守哑者”,聚居于西南深山,终生不发一言,仅以手势、眼神、脚步轻重传递心意。有人问其缘由,他们лишь摇头,指向耳朵,再指心口,最后做出撕裂的动作。
他们不说,是因为他们记得太清楚。
记得那些曾因“听错”而被烧死的人,在火焰中最后喊出的不是求饶,而是更清晰的质疑;
记得那些被灌入强制音频的母亲,在癫狂中仍试图为婴儿哼唱不属于系统的摇篮曲;
记得有一个小女孩,在被割去双耳前,笑着说:“我知道你们想让我听不见,可我现在反而听得更多了。”
承光年岁渐长,听力却愈发敏锐。他能在风吹树叶的沙沙声中分辨出三十年前某场集会的口号;能在婴儿啼哭中听出前世未说完的遗言;甚至能在自己的心跳里,捕捉到闻婴残留的节奏。
一日午后,他独坐槐树之下,闭目养神。忽觉胸口微热,低头一看,怀中海螺竟自动开启,从中飘出一缕极细的声丝,如烟似雾,升腾而起,在空中凝成三个字:
**“谢谢你。”**
他笑了,轻声回应:“该说谢谢的,是我。”
谢婉走来,递给他一碗药汤。“你的耳朵太累了。”她说,“有时候,也该让它休息。”
他点头,却并未喝下。他知道,一旦真正安静下来,或许就会错过下一个觉醒的契机。
傍晚时分,岛上来了一位陌生僧人。
他衣衫褴褛,手持一根铜铃,铃舌已被摘除,只剩空壳。他不说话,只将铜铃置于地上,然后盘膝而坐,闭目冥想。良久,那无舌之铃竟自行发出嗡鸣,音色苍凉,似有万千冤魂附着其上。
承光走近,蹲下身子,凝视那铃。
“你想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