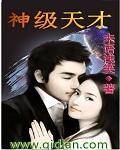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斗罗:修玄君七章,成慈怀药王! > 第二百六十章 天外客(第1页)
第二百六十章 天外客(第1页)
贝克兰德,这座万都之都,此刻正被恐慌与混乱的潮水反复冲刷。
尖叫声、哭喊声、物品碰撞碎裂声、以及远处偶尔传来的、绝非寻常的爆炸轰鸣,交织成一曲文明秩序崩塌的混乱交响乐。
人流如同受惊的兽群。。。
我蹲在记得花主藤旁,指尖轻轻拂过那朵新生的白花。它开得极静,像一缕未落地的雪,花芯里的字迹微微发亮:“下一个故事,你想听谁的?”风从山谷口吹来,带着初春的湿意和去年枯叶腐烂后的泥土香。我忽然觉得这句话不是问我,而是问整个山谷??问那些守言人、问沈知行、问周临走过的每一寸土地。
我没有回答。
因为我知道,答案总会自己走上来。
三日后,石阶尽头出现了一个人影。
她走得极慢,每一步都像是试探着地面是否真实。灰布外套洗得发白,肩头缝着一块深色补丁,背上的帆布包鼓鼓囊囊,边角磨出了毛边。她站在回声屋前,没有敲门,也没有喊人,只是站着,目光落在记得花架上,嘴唇微微动了动,仿佛在默念什么。
林雪最先看见她,端着粥碗的手顿在半空。她认出来了??是许知远提到过的那位母亲,王小舟的母亲。那个曾在信中写道“我不求翻案,只想让他最后的日子被人记得”的女人。
我放下剪刀迎出去。她没看我,只低声说:“我来找一棵会开花的藤……听说,它能听见死人的话。”
“它是听见活着的人。”我说,“然后替你们转达给不在的人。”
她眼眶立刻红了,手指紧紧攥住背包带子,指节泛白。她想哭,但忍住了,像是已经习惯了把眼泪压在喉咙里多年。
我请她进屋坐下。沈知行正在整理《共心录》的副本,见她进来,默默起身泡了一杯茶。水汽升腾时,他轻声说:“您儿子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
她猛地抬头:“可没人听我说过!学校说他是意外,警察说没证据,心理老师说我‘情绪不稳定’,连亲戚都劝我别闹了……‘人都没了,争这些做什么?’”她的声音陡然拔高,又迅速低下去,像一根绷到极限的弦终于松了劲,“可我只是想知道……他最后疼不疼?冷不冷?有没有人拉他一把?”
屋里很静。窗外记得花轻轻晃动,一片叶子悄然飘落,正好落在她膝上。
我问:“您愿意说吗?我们可以听。”
她咬着下唇,许久,才从包里掏出一个铁皮盒子。打开后,是一叠皱巴巴的纸??全是她写给儿子却从未寄出的信。有的用铅笔写,字迹被泪水晕开;有的贴着照片,角落写着“这是你最爱吃的糖,妈又买了”;最底下还有一件校服袖子,边缘烧焦了,她说:“那天火化场让我挑遗物,我就剪了这一块回来。”
她开始讲。
讲王小舟小时候怕黑,总要妈妈握着手才能睡;讲他初中开始被同学排挤,回家只说“没事”;讲他最后一次回家,饭桌上突然问:“妈,如果我不在了,你会不会比现在更难过?”她当时笑着骂他胡说,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他在求救。
“我那时候为什么没抱住他?”她哽咽,“为什么不说一句‘你说,我在’?”
话音落下,记得花主藤剧烈震颤,一朵紫红色的花骤然绽放,花瓣缓缓展开,露出内里的文字:
>“妈,我不是怪你没说话。
>我只是太累了,想有人替我说完那些没出口的话。”
她扑跪到藤前,双手颤抖地抚摸那朵花,眼泪砸在泥土上。沈知行轻轻将铁盒中的信取出来,放入竹篓,准备由下一任信使送往周临所在的方向??他正前往西南山区,拜访另一位失独母亲。
当晚,山谷降下细雨。
雨水顺着藤蔓滑落,记得花却未闭合,反而释放出微弱荧光,如同夜河倒悬。谛听草叶片舒展,在雨中轻轻摆动,仿佛在接收某种频率。
第二天清晨,我发现墙上多了一行新刻的字,墨迹未干:
>“倾听不是拯救,是归还??把属于他们的声音,还给他们自己。”
这时,陈昭匆匆赶来,手里攥着一份外地报纸。头版标题刺目:
>《“安静五分钟”计划遭质疑:浪费课时、助长消极情绪》
>??某教育专家称,“沉默训练”可能导致学生“沉溺负面情绪”,建议取消或改为“积极心理引导课”。
我看完冷笑。那些从未听过孩子哭泣的大人,永远在教别人如何“振作”。
沈知行却平静地剪下这篇报道,贴在回声屋外墙上,旁边附一张便签:
>“当有人指责沉默危险时,请问他:是你害怕听见,还是真为孩子着想?”
当天下午,林晚从第一驿站传回消息:一位曾参与霸凌王小舟的学生家长主动来到社区中心,要求“接受倾听”。他说儿子最近频繁做噩梦,醒来总喊“对不起”,但他一直以为是学习压力大。“直到我在新闻里看到‘慈怀行动’,我才意识到……有些错,不能靠成绩抵消。”
我们立即安排许知远作为倾听者前往。出发前,周临的明信片恰好抵达:
>“我在云南一座小学做完分享。有个孩子课后追出来,塞给我一张纸条:‘我每天装开心,其实我想妈妈回来。’
>我陪他坐了四十分钟,什么也没说。
>他走的时候笑了,说:‘原来不说也可以轻松。’
>这就是种子在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