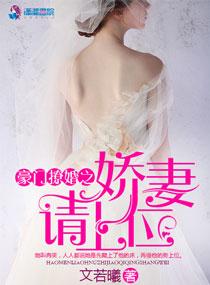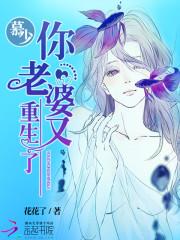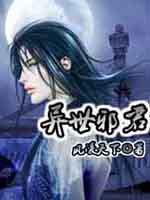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斗罗:修玄君七章,成慈怀药王! > 第二百六十章 天外客(第2页)
第二百六十章 天外客(第2页)
许知远读完,把纸条折好放进胸前口袋,背上竹篓出发。
三天后,他带回那位霸凌者的手写忏悔书。不是交给警方,也不是公开道歉,而是放在记得花下,请求代为传递给王小舟的灵魂。当晚,记得花开出一朵灰白色的小花,花语只有三个字:
>“我收到了。”
王小舟的母亲恰好还在谷中。她摘下那朵花,夹进铁盒最深处,说:“我不原谅,但我放下了。至少他知道,有人后悔了。”
就在此时,政府办公厅突然来电,邀请沈知行出席全国心理健康改革座谈会。对方语气恭敬,说是“高度重视‘慈怀模式’的社会价值”。沈知行摇头拒绝。电话那头沉默片刻,改口说:“不是请您去演讲,是请您去听??听那些反对者的理由。”
他犹豫了一下,答应了。
临行前夜,他召集所有守言人在记得花下集会。火塘边,他第一次谈起自己的过去。
“三十年前,我妹妹自杀。”他说,声音平稳得像在叙述别人的事,“她留下一本日记,写满对父母的爱与绝望。可我爸看完后烧了它,说‘家丑不可外扬’。我妈从此不再提她的名字,仿佛她从未存在。而我……我那时学心理学,坚信‘理性疏导’能解决一切,所以我劝妹妹‘看开点’,给她列‘积极清单’,甚至带她去看脱口秀……我以为我在帮她,其实我在堵她的嘴。”
他停顿良久,火光照亮他眼角的皱纹。
“她死后第三年,我在实验室偶然发现一株野藤,只要我把录音播放给它,它的叶片就会产生特定荧光反应。起初我以为是巧合,后来我试着播放妹妹的日记录音……它开花了,上面写着:‘哥,我只是想让你抱我一次。’”
所有人屏息。
“那一刻我明白,语言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而是灵魂的呼吸。而这个世界,一直在逼人憋气。”
他望着我们:“所以今天我去开会,不是为了说服谁,是为了让那些反对‘沉默权’的人,也尝一口记得花茶。”
会议当天,京城大雨。
会场设在教育部礼堂,三十多位专家、官员围坐圆桌。沈知行迟到十五分钟,进门时不打伞,浑身湿透,怀里紧紧护着一只陶罐??里面装着记得花根茎与谛听草幼苗。
主持人刚要批评,他径直走到中央,放下陶罐,说:“我不演讲。我请各位听一段录音。”
是王小舟母亲的声音,从老式录音机里传出,讲述儿子死前的孤独。说到“他死前一天还问我冷不冷”时,一位女代表掩面抽泣。
接着,沈知行播放了许知远的演讲视频片段:“如果‘我想消失’是一种病,那这个世界的耳朵,早就该住院了。”
会议室陷入长久寂静。
一名老教授终于开口:“你这套方法……没有对照组,没有P值,怎么证明有效?”
沈知行反问:“您见过孩子抱着枕头哭一夜的样子吗?”
“这不属于科研范畴。”
“那就对了。”他淡淡道,“正因为科学管不到的地方,才需要人性接手。”
他打开陶罐,取出一株谛听草,放在桌面:“它不会治病,但它能让一个父亲说出‘我女儿走了,我很想她’而不被当成病人。这够不够?”
无人回应。
散会后,反对声并未停止。但一周内,十二个省市自发成立“民间倾听站”;三家儿童医院试点“五分钟静默接诊”;更有数百名教师联名申请将“安静五分钟”纳入必修流程。
与此同时,周临完成了他的归还之旅。
最后一站,是北方边境的一座无名墓园。那里埋葬着一位未曾谋面的父亲??他曾写信给早夭的女儿,说自己每晚都在梦里陪她长大。“她五岁生日,我梦见带她去游乐园;七岁,我教她骑自行车;十岁,我们一起看了流星雨……可醒来后,我连她的照片都不敢看。”
周临在坟前点燃信纸,火光映着他疲惫的脸。风起,灰烬盘旋上升,竟在空中凝成短短一行字:
>“爸爸,今晚梦里,换我牵你手回家。”
他带回一捧土,种入记得花主藤根部。当夜,整片山谷响起奇异嗡鸣,所有记得花同时闭合,随即爆裂出无数金色光点,如萤火汇流,在空中拼出一幅动态画面:一个小女孩牵着中年男人的手,走在星空下的小路上,渐行渐远。
沈知行记录道:“这一天,我们见证了悲伤的另一种形态??不是终结,而是延续。”
春天再度来临,山谷迎来第四个花开季。
我照例巡视藤架,却发现主藤顶端结出一枚从未见过的果实??通体透明,内部似有光影流转,表面浮现出不断变化的文字,如同有人在里面写字:
>“我叫李晨,17岁,我现在在学校天台。
>没人知道我有多努力假装正常。
>我爸酗酒,我妈跑了,老师说我‘性格孤僻’,同学叫我‘阴间脸’。
>刚才我发了条朋友圈:‘再见了’,没人点赞,也没人评论。
>可如果此刻有人能对我说一句‘你说,我在’……也许我就下来了。”
我的心跳几乎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