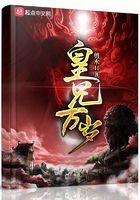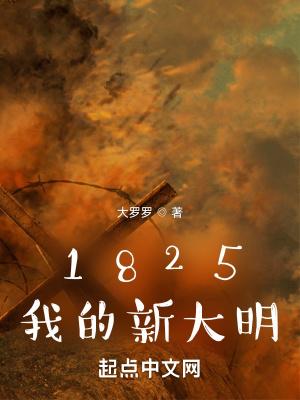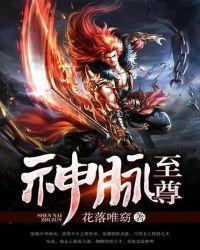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我要当大官 > 第二百零七章 省内省外两幅天地(第2页)
第二百零七章 省内省外两幅天地(第2页)
殿外甲胄铿锵,两名神机营武士入内,将徐知远押走。临出门前,徐知远忽然回头,盯着李燕:“你会后悔的。没有我们这些人牵线搭桥,外资撤离,工厂停工,新政立刻崩溃。到那时,百姓饿殍遍野,看你还能不能讲这些漂亮话!”
李燕目送他离去,久久未语。
谢文丽悄然走入,轻声道:“他的话,未必全错。恒昌商号查封后,已有三家外资纺织厂宣布暂停增资,北方数万织工面临失业。”
“那就让他们停。”李燕坐回椅中,神色疲惫却不屈服,“宁可慢一点,也不能让国家的命脉攥在叛徒手里。告诉财政大臣,启动‘国民工业扶持基金’,优先贷款给本土企业。另外,下令全国公立学堂增设‘经济实务课’,教年轻人办厂、记账、谈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资本家,而不是依赖洋人的施舍。”
谢文丽点头欲退,却被他叫住。
“还有一件事。”李燕从抽屉取出一封信,“刚才邓伦送来,是旅顺那边传来的密报。俄军虽已撤离,但在撤走前,炸毁了东港码头的主油库,并在地下埋设了延时引信装置,预计十日内引爆,目标是新建的海军补给站。”
谢文丽震惊:“他们想毁掉我们的后勤根基!”
“不仅如此。”李燕将信递给她,“情报显示,引爆装置由一名化名为‘灰鸦’的德籍工程师设置,此人曾在克虏伯工作,擅长隐蔽爆破。更重要的是……他现在就在北京。”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今天早上,京师大学堂收到一笔匿名捐款,资助设立‘海洋科学研究所’,署名是‘一位敬仰贵校精神的外国友人’。金额刚好是五千银元??与‘灰鸦’在柏林领取的任务酬金完全一致。”
谢文丽倒吸一口冷气:“他是冲着学术机构来的。一旦研究所成立,他便可合法入境,以‘技术顾问’身份接近军方项目。”
“没错。”李燕站起身,眼中寒光闪动,“这次,我们不抓,不审,不曝光。我要让他自己走进陷阱。”
三日后,京师大学堂正式宣布接受捐赠,并公开欢迎“国际专家”参与筹建。报纸刊登消息,称该所将研究“潮汐发电”与“海底电缆铺设”,极具前瞻性。同时,校方发布招聘启事,诚聘精通“地质勘探”与“隧道工程”的外籍技术人员。
不到四十八小时,一名自称“卡尔?穆勒”的德国工程师递交申请,附有柏林工业大学推荐信及多国项目履历。经神机营核查,此人护照系伪造,且右耳后有一道陈年烧伤疤痕??正是“灰鸦”的标志性特征。
李燕亲自批准聘用。
“穆勒先生”顺利入境,入住使馆区一家安静旅馆。他每日前往大学堂“办公”,与教授讨论“科研方案”,表现极为专业。然而,他未曾察觉,实验室角落的通风管内,藏着微型摄像机;他使用的电脑,已被植入追踪程序;他每一次拨打电话,信号都会被同步转送至神机营监听中心。
第七日夜里,他终于行动。凌晨两点,他借口“检查设备”,独自进入地下储藏室,从工具箱夹层取出一枚手掌大小的黑色装置,开始对接电源线路。摄像头清晰拍下了他的每一个动作??拧开面板、接入导线、输入密码。
就在他按下测试键的瞬间,灯光骤灭,警报响起,铁门自动锁死。数十名便衣特工破门而入,枪口对准他的头。
“卡尔?穆勒?”邓伦走上前,用德语说道,“或者,我该称呼你为‘灰鸦’?”
那人僵在原地,片刻后苦笑:“你们……早就知道了?”
“从你汇款那天起。”邓伦收起枪,“你以为我们真会把军事设施交给外国人设计?这场戏,就是为了等你现身。”
次日上午,外交部召开紧急记者会。李燕亲自主持,现场展示“灰鸦”携带的爆炸装置、伪造证件及全部通讯记录,并当场播放其作案视频。他面对镜头,语气沉重:“这不仅是针对我国防设施的袭击,更是对科学精神的亵渎。他们假借‘合作’之名,行破坏之实;打着‘援助’旗号,藏杀机于无形。我在此郑重警告:任何企图伤害中国的外国人,无论披着何种外衣,都将受到法律严惩!”
国际舆论再次哗然。德国政府迅速表态,称“穆勒”系rogueagent,已与其断绝关系;法国《世界报》发表社论:“当殖民思维不死,和平便永远只是幻象”;就连美国国务院也发布旅行警告,提醒本国公民“避免参与敏感技术转移”。
与此同时,国内民心空前凝聚。学生们发起“科技清源运动”,要求审查所有涉外科研合作项目;科学家联名签署《科研伦理公约》,承诺“绝不让实验室成为战场”;更有数百名海外留学青年主动回国,誓言“用知识报国”。
风波渐息,李燕却未松懈。他知道,敌人不会就此罢休。
一个月后,西北传来急报:新疆伊犁地区发现非法武装集结,装备精良,使用俄制步枪与无线电台。更令人警惕的是,当地一名汉族乡绅供述,曾有人许以重金,请他在边境绘制“地形草图”,并特别标注水源与驻军位置。
李燕立即下令军机处介入,同时派遣谢文丽以“国民议会观察员”身份赴疆调查。临行前,她问:“你怀疑是‘白狐’余党?”
“不止。”李燕望着地图上那片广袤边疆,“是整个网络。他们从未消失,只是从京城转移到了边陲,从朝堂潜入了民间。但这一次,我们不会再给他们喘息之机。”
他提起朱笔,在奏折上写下八个大字:**斩草除根,寸土不让。**
夜深人静,李燕独坐书房,窗外秋雨淅沥。他翻开一本旧日记,那是他年轻时在街头当差记录民情的手札。某一页写着:“今日见一老妪乞食不成,遭衙役鞭打。问其故,曰‘无户籍,不算人’。吾心痛如割。若有一日得志,必使人人都能抬头走路。”
他合上日记,抬头望月。
风依旧穿过廊柱,铜铃轻响,如同岁月低语。而在这声响之中,一个新的时代,正踏着风雨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