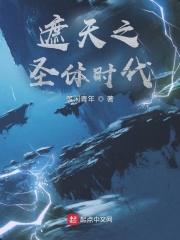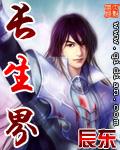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炮灰的人生2(快穿) > 2460高嫁的贵夫人 一(第3页)
2460高嫁的贵夫人 一(第3页)
他浑身一震。
两人对视良久,窗外月色渐斜。
临别时,太子忽然唤住她:“林姑娘,你说……如果有一天,我也成了那个高座之人,会不会也变成自己曾经质疑的对象?”
林知意回头,淡淡一笑:“会。但只要你还记得今晚这个问题,就还有救。”
回到西北后,她立即调整战略。不再追求大规模集会,转而推动“微问运动”??鼓励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植入一个小问题。卖菜妇在秤砣底部刻“此秤准否”;教书先生在学生作业批语里夹一句“此答果真唯一?”;甚至连寺庙和尚都在往生咒旁添上一行小字:“轮回由谁定?”
这些问题微小如尘,却无处不在,防不胜防。
夏日来临,黄河决堤。朝廷依旧迟缓应对,直到淹没三州十八县,才勉强下令赈灾。而此时,“夜读会”早已通过“海语符号”与“骨书系统”构建起独立情报网,提前组织救援,挽救数千性命。灾民感激涕零,纷纷跪拜称“林先生活我”。
名声再度高涨之际,林知意却突然宣布解散“夜读会”总部。
众弟子哗然。
“这不是失败,是进化。”她在最后一次集会上说道,“‘夜读会’只是一个名字,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无数个名字。从今天起,你们各自为火种,不必再向我汇报,不必再守统一章程。只要你还在教人提问,你就是‘夜读会’。”
她摘下颈间铁笔徽章,投入火堆。火焰腾起,映红众人脸庞。
“火种不在组织,而在问题本身。”
秋分再度临近,距离慈恩寺大会整整一年。民间自发举行“万问周年祭”,万人齐聚各地高地,面向北方默念那一夜的问题。有人点燃纸船放入江河,载着写满疑问的竹片顺流而下;有人攀上高山,在岩石上凿出巨大“问”字,远望如血。
而在皇宫深处,皇帝翻阅各地奏报,眉头紧锁。今年的秋收数字异常平稳,可民间舆论却前所未有的躁动。连一向恭顺的皇子们也开始在诗会上引用《怀疑的权利》中的句子,美其名曰“思辨之趣”。
最令他不安的是,昨夜寝宫屋顶发现一张布条,上面写着:
>“陛下日食三餐,可知百姓一日几餐?”
无人知晓是如何送入禁地。
他召见太子,厉声质问:“是不是你纵容那些刁民胡闹?”
太子跪地,神情坦然:“儿臣只是设立谏询司,收纳民意。若连听一听都不肯,又如何知天下疾苦?”
皇帝怒极反笑:“好啊,你现在倒学会替他们说话了?”
“儿臣只是在履行储君之责。”太子抬头,“况且,这些人并未作乱,只是在问。而问,本是人的本能。”
皇帝久久不语,最终挥袖而去。
当晚,他独自登上观星台,仰望苍穹。北斗依旧如铁笔悬天,寒光凛冽。
他忽然想起二十年前,一位老道士曾对他预言:“陛下将治盛世,然有一劫难避??非兵祸,非天灾,乃‘人心之问’。一旦万民皆思,江山虽固,亦将动摇。”
当时他嗤之以鼻。
如今,那问声已如潮水漫过堤岸,无声无息,却无可阻挡。
林知意站在雪山之巅,手中握着一块新制成的铁笔徽章??这次是用陨铁打造,黑沉如夜。她俯瞰大地,万里河山笼罩在薄雾之中,仿佛仍在沉睡,却又隐隐搏动着觉醒的脉搏。
阿满走来,轻声问:“下一步去哪里?”
她将徽章轻轻抛入风中,任其坠向山谷。
“哪里有沉默,就去哪里。”
“因为沉默,才是最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