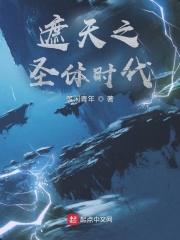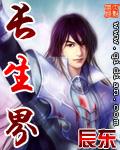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炮灰的人生2(快穿) > 2460高嫁的贵夫人 一(第2页)
2460高嫁的贵夫人 一(第2页)
>十家灶冷九,只剩狗守门。”
这首歌谣迅速传遍十郡,连京中贵妇绣花时都在哼唱。户部尚书不得不奏请开仓赈济,以免民变。皇帝怒斥其“妄增国耗”,却终究被迫松口。
林知意在西北听到消息,终于露出久违笑意:“现在,连瘟疫都在替我们发声了。”
然而危机也随之逼近。
清明前后,一名叛徒被捕。他曾是“夜读会”骨干,因家人被胁迫而供出部分联络方式。一夜之间,七个据点遭突袭,二十三人被捕,其中包括编写《税吏之影》的盲文书匠陈伯。此人双目失明,靠心记口述完成数十万字民间赋税史,被捕前最后一句话是:“把我舌头割了也没用,我已在三个徒弟脑中种完了全篇。”
林知意连夜召集残余弟子,宣布进入“灰烬模式”:所有活动暂停三个月,人员分散隐蔽,仅保留最低限度的情报流动。她亲自焚毁近三年来的笔记与名单,将最后一份《万问录》副本封入千年古柏树洞,并以蜂蜡密封。
就在她准备撤离学堂之际,阿满带来一封密信??来自宫中太监总管,曾是苏禾旧友。信中只有一行字:
>“东宫欲见你,月圆之夜,紫宸殿侧门。”
她怔住。
太子要见她?那个曾在她信上批下“准”字的男人,如今竟主动邀约?这或许是陷阱,也可能是转机。
她思索整夜,最终决定赴约。
月圆当空,紫宸殿外槐影婆娑。林知意换上粗布男装,由太监引路,穿过重重宫墙。沿途所见,皆是森严戒备,巡逻侍卫比往日多出三倍。直至偏殿暖阁,才见太子独坐灯下,面容憔悴,眼下乌青。
“你来了。”他抬头,声音沙哑,“我知道你不该来,可我必须见你一面。”
林知意不动:“殿下不怕这是谋逆之举?”
“若连见一面质疑者的勇气都没有,我也不配坐在这东宫之位。”太子苦笑,“你知道这三个月我做了什么吗?我把你们那本《万问录》抄了一遍,整整三十六问,一字不漏。然后烧了它。”
她挑眉。
“烧给列祖列宗看。”他低声道,“我想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天经地义’,正在逼死这个国家的良心。”
林知意沉默片刻:“那你打算怎么办?继续做笼中太子,等哪天父皇觉得你‘不够忠顺’,便换一个更听话的?”
“我在等。”太子直视她,“等一个问题足够痛,痛到连皇帝也无法装睡。”
“比如呢?”
“比如……”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悲愤,“一个月前,西北大旱,朝廷拒开义仓,说是‘恐耗储备’。可就在同一天,内务府却拨银十万两,为贵妃修建温泉行宫。有个县令实在看不下去,上疏直言,结果被贬为驿卒,押送去漠北喂马。途中冻死在雪地里,尸体被狼啃食一半。”
林知意呼吸微滞。
太子缓缓从袖中抽出一张纸:“这是他临终前托人带出的最后一封信,我没让它进奏折堆。你想听听吗?”
纸上血迹斑斑,字迹歪斜:
>“吾非为己鸣冤,只为天下饥民一问:
>**当权者以百姓血汗建享乐之宫,却以‘国库不宜轻动’拒救饿殍,此谓何理?
>若此即为‘治国之道’,宁做草莽贼,不做庙堂臣。**”
暖阁内长久寂静。
良久,林知意开口:“你若真想变,就不该只藏一封信,而应让它响彻朝堂。”
“可我说了有用吗?”太子苦笑,“每次我提‘宽政’‘减税’,父皇就说:‘你太年轻,不懂权衡。’可我不懂的是,为何非要等到民变四起,才肯低头?”
“因为你还没让他感受到痛。”林知意冷冷道,“权力只会回应威胁,不会回应道理。”
太子猛地抬头:“你要我造反?”
“我要你成为问题本身。”她逼近一步,“当你站在龙椅前,不再是那个温顺储君,而是第一个向皇帝发问的儿子??那时,变革才会真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