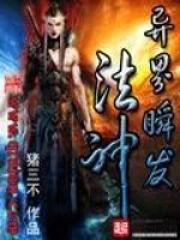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多我一个后富怎么了 > 292 革新(第1页)
292 革新(第1页)
一个问题没说好,新的问题就出现了。
来自铜市的马志豪看着表情没什么波澜的俞总,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铁牛集团与市里的合作虽然还没官宣,但基本上板上钉钉,就差最后一步的协议签署,而且两边。。。
车轮碾过戈壁滩的碎石,发出沉闷而规律的响声。林远已连续驾驶十一个小时,眼睛干涩发烫,可他不敢停。巴特尔的消息越来越急:老人从三天前开始昏迷,间歇清醒时只反复念叨一句话??“我要把《江格尔》唱完。”
那是蒙古族最伟大的英雄史诗,长达十八万行,巴特尔是最后一位能完整传诵十二章的“江格尔奇”。如今他年逾九旬,记忆如沙漏般流逝,唯有在梦中还能听见少年时代师父的吟唱。
林远翻出车载录音箱中最厚的一卷磁带,标签上写着【致苏芸?第17卷】,指尖轻轻摩挲着那行字迹。他知道这盘带子终将不属于他一个人。等录下巴特尔的声音,他会剪下一小段,封存在一个陶罐里,埋进侗寨那棵古杉树下??作为两个民族之间无声的盟约。
抵达新疆边境小镇已是凌晨三点。月光下的草原泛着铁灰色,远处毡房零星亮着灯。林远凭着记忆找到巴特尔家的蒙古包,刚掀开门帘,一股浓重的草药味扑面而来。屋内围坐着七八个亲属,人人面色凝重。见他进来,一名中年男子起身握住他的手:“你来得正好……父亲刚才醒了,说要见‘那个听声音的人’。”
巴特尔躺在火炕边的羊毛褥子上,瘦得几乎脱形,双颊凹陷,但眼神仍锐利如鹰。他看见林远,嘴唇微微颤动,用极轻的声音说了句蒙古语。身旁的儿子翻译道:“他说,你终于来了,我等了你三年。”
林远跪坐在炕沿,打开设备,调试麦克风增益。他知道这种时候不能催促,只能等待。他取出随身携带的陶铃??这是侗寨长老送他的信物,摇了一下,清脆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荡开。巴特尔的眼睛忽然亮了,喃喃道:“这是……南方的风铃?”
“是啊。”林远轻声回应,“它会把您的声音带到很远的地方去。”
老人闭上眼,深吸一口气,喉咙里缓缓涌出一段低沉苍凉的旋律:
>“苍天睁开金色的眼,大地抖落霜雪的衣;
>白鬃烈马踏云而来,英雄江格尔举起战戟……”
歌声虽弱,却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仿佛整片草原都在共鸣。屋内众人纷纷低头合掌,有妇女悄悄抹泪。林远屏住呼吸,将录音电平调至最高灵敏度,生怕错过任何一个音节。这一章讲的是江格尔少年时斩杀恶魔、建立宝木巴国的故事,传说中每一代传人都必须在临终前完整复述,否则灵魂无法归于圣山。
唱到第七段时,巴特尔突然咳嗽起来,气息紊乱。家人急忙上前扶他喝水,劝他休息。但他固执地推开杯子,坚持要继续。林远递上一杯温热的奶茶,低声说:“您慢慢来,我们有的是时间。”
老人笑了笑,目光落在角落里的马头琴上。“那是我十七岁那年亲手做的。”他说,“那时候师父告诉我,真正的史诗不在耳朵里,在骨头里。你要让它长进你的肋骨,变成心跳的一部分。”
林远点头:“我现在懂了。就像侗族的老歌师说,得先学会做梦。”
巴特尔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你也听过这话?”
“不同的山,同一条河。”林远微笑,“他们都相信,有些话只能由祖先在梦里教。”
那一夜,巴特尔断续唱了四个小时,完成了第八至第十章的核心段落。每当力竭,他就闭目养神片刻,再睁开时,仿佛换了个人,声音竟又稳了几分。林远注意到,每次重启吟唱前,老人总会轻抚额头,像是在回忆什么画面。
“您是不是……梦见了师父?”林远试探着问。
巴特尔点头:“他站在我床边,穿着蓝绸袍,手里拿着鼓槌。他说:‘你还欠三章,别让它们断在你这儿。’”
林远心头一震。他知道这不仅是临终幻觉,更是一种文化传承特有的精神机制??当记忆濒临崩溃,潜意识会自动激活最深层的语言模块,借由梦境重构失落的文本。这正是“remember-me”系统最难模拟的部分:情感与信仰如何赋予语言生命力。
天快亮时,巴特尔再次陷入昏睡。医生检查后说情况暂时稳定,但随时可能离世。林远走出蒙古包,站在草原上望着东方渐白的天空。寒风吹起他的衣角,他忽然觉得无比疲惫,却又异常清醒。他拿出日记本,在新的一栏写下:**语言不是工具,是活的生命体。它饥饿时吞噬遗忘,饱足时哺育未来。**
接下来三天,林远白天守在蒙古包外,夜晚则整理已录下的音频。他发现巴特尔的吟唱中夹杂着大量即兴变奏,同一段故事每次讲述都有细微差异??这才是口传史诗的本质:不是固定文本,而是流动的传统。他决定放弃标准化转录,改为建立“多版本语料库”,允许同一章节存在多种演绎形态。
第四天傍晚,奇迹发生了。巴特尔突然坐起,神志清明,要求沐浴更衣。家人惊疑不定,却依言照办。换上洁净的白色长袍后,老人主动示意林远开机。
“我要唱最后一章。”他说,“关于死亡本身。”
林远屏息凝神,按下录制键。
巴特尔的声音前所未有的平静,像秋日湖水般澄澈:
>“勇士终将卸下铠甲,骏马也会老去;
>但歌声不会熄灭,因为它不属于任何人??
>它属于风,属于星空,属于孩子睡前睁大的眼睛。
>当最后一个传人闭上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