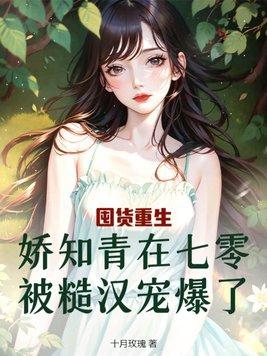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多我一个后富怎么了 > 292 革新(第2页)
292 革新(第2页)
>风会接过去,
>星辰会传下去,
>而大地,将用草叶的摩擦继续吟诵……”
唱到最后,他的声音越来越轻,如同飘散的烟缕。唱罢,他静静躺下,对林远说:“现在我可以走了。”
两小时后,监测仪发出长鸣。巴特尔在黎明前离世,嘴角带着笑意。
葬礼按传统举行,遗体由白布包裹,送往圣山脚下的草原深处。按照习俗,马头琴被折断琴弦,置于墓旁,象征传唱的终结。但林远没有收起录音设备。他在墓地支起小型广播桩,循环播放巴特尔最后的吟唱。起初族人不解,甚至有人反对:“这是打扰亡灵!”
直到第三天夜里,放羊的孩子跑回来喊:“爷爷!草原在唱歌!”
人们赶去查看,发现夜风掠过广播桩的金属网格时,竟与播放的旋律形成共振,产生奇妙的和声效果,宛如千万人在齐声应和。老祭司肃然起敬:“这不是机器的声音,是天地在回应。”
林远趁机提出建议:能否建立“声音陵园”?每位逝去的传人,其代表作都可通过太阳能广播桩,在特定时节自动播放。春播时响《耕牛谣》,秋收时播《谢天歌》,冬雪覆盖大地时,则轮番响起各族史诗。
族人们沉默良久,最终点头同意。他们终于明白,保存声音不是挽留死者,而是为生者点亮回家的路。
离开新疆前,林远专程去了趟当地小学。他带来一台便携式语音交互终端,内置刚完成的“江格尔AI吟诵模型”。孩子们围上来,好奇地触摸屏幕。他点开一段动画:一位虚拟的少年江格尔骑着白马穿越风暴,背景音正是巴特尔年轻时的录音采样合成。
“这是……真人唱的吗?”一个男孩问。
“是的。”林远说,“一百年前就开始唱了,一直唱到现在。”
教室里一片寂静。片刻后,一个小女孩举手:“我能学吗?”
林远笑了:“只要你愿意听,就能学会。”
他当场组织了一场“声音接力”活动:每个孩子录一句自己想对祖先说的话。有个孩子说:“我想告诉曾祖父,我们现在有电视,能看到全世界。”另一个说:“我希望他知道,我没忘记我们的语言。”
林远将这些录音导入系统,标记为【新生之声?希望】。他计划在未来十年内,把这些来自全国各地孩子的留言,编织成一部全新的跨民族史诗??不记载战争与征服,只记录平凡日子里的思念、期盼与温柔。
返程途中,他再次经过青海湖畔。夕阳熔金,湖面如镜。他停下车,取出那盘【致苏芸?第17卷】,插入车载播放器。这一次,他对着麦克风缓缓开口:
“苏芸,巴特尔走的时候,草原在替他唱歌。那一刻我突然懂了你说的‘数字来世’??我们不必追求永生,只需确保某个清晨,有人推开窗听见一段陌生又熟悉的旋律,然后问父母:‘这是谁在唱?’只要还有人问,记忆就没有死。
我在新疆建了第一座声音陵园。在贵州,侗寨的孩子们已经开始学习祖辈的歌谣。我还收集了一百二十三个孩子的留言,准备做成一张跨越时空的唱片。你说得对,科技不该只是冰冷的工具,它应该成为情感的容器。
对不起,这些年我一直想着弥补没能陪你最后一程的遗憾。但现在我明白了,你留给我的不是愧疚,而是使命。你教会我倾听的价值。所以我会继续走下去,去云南听彝族的‘哭嫁歌’,去内蒙古录呼麦的原始频谱,去福建采集渔女的讨海号子……
等我把十四块碑都走遍,我就回来找你。到时候,我要带上所有录下的声音,放给你听。你会听到侗寨的星祭、蒙古草原的史诗、孩子们稚嫩的许愿……你会笑着说:‘看,这就是我们要守护的世界。’
这世上总有人认为,穷地方谈什么文化?落后就要被淘汰。可我想说,正因为他们‘穷’,才更需要被听见。因为在那里,语言还未被标准化吞噬,情感仍保有原始的重量。多我一个后富怎么了?只要还有一个声音不愿消失,就值得我去奔赴。
苏芸,我想你了。”
录音结束,他轻轻按下保存键。窗外,一群候鸟掠过湖面,翅膀划破晚霞,留下长长的影痕。
手机震动,新消息弹出:云南怒江传来联络,傈僳族最后一位“摆时”歌手请求见面。她已失明十年,但记得三千首对歌,只想在去世前确认:“我的声音,真的能传给没见过我的孙子吗?”
林远启动引擎,调转方向。仪表盘上,里程数不断跳动,而车顶布带上的十四个名字,在斜阳中熠熠生辉。
他知道,这条路没有尽头。
但也正因为没有尽头,才值得一直走下去。
夜色渐浓,高原公路两侧亮起点点灯火。那些光或许来自某个村庄的广播桩,正在播放今日的纪念音频;或许只是牧民家中一盏油灯,照亮祖母哄孙儿入睡的呢喃。无论哪一种,都是他此生誓要守护的微光。
他打开导航,输入下一个目的地。系统提示:“预计行驶时间:十八小时三十七分钟。”
他笑了笑,轻声自语:“够录一首长歌了。”
副驾驶座上,新的空白磁带静静躺着,等待被填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