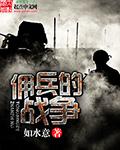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剥夺金手指(清穿) > 441第 441 章(第2页)
441第 441 章(第2页)
全班齐声朗读。
然后,一个孩子举手:“老师,这样说会被惩罚吗?”
老师摇头:“在这里不会。因为诚实比正确更重要。”
又一个孩子站起来:“可如果我说‘我恨这个世界’,也算诚实吗?”
教室安静了一瞬。
老师走过去,轻轻抱住她:“算。而且,谢谢你告诉我。”
莲心站在门口,泪流满面。
她忽然明白,真正的教育不是灌输真理,而是教会人如何面对未知;不是消除疑问,而是守护那份敢于提问的勇气。
梦醒时,东方既白。
她起身梳洗,煮茶焚香,照例打开院门。门外已有人等候??不是求药者,也不是官员,而是一位年迈的教书先生,手持残破教案,颤巍巍递上前。
“我教了五十年书。”他说,“教忠孝仁义,教克己复礼,教人成为‘该成为的样子’。可昨夜,我梦见我的学生们都在哭,因为他们从没机会做自己。我想……我想重新开始。”
莲心接过教案,翻开一页,上面密密麻麻写满批注,红笔划去的句子比保留的更多。她在最后一页看到一句话,墨迹新鲜:
**“或许,我也曾是个孩子。”**
她将教案还给他,只说了一句:“去吧,去找那些愿意听你说真话的学生。”
老人深深鞠躬,转身离去,脚步竟比来时轻快许多。
日近正午,江南驿马疾驰而至,送来一封密函。拆开一看,竟是共谐城遗址管理处所发,附图一张:那尊金色问号雕像周围,已建成一座开放式广场,名为“疑之园”。每日清晨,居民自发聚集,进行“无声问答”??一人站立中央,用手势或文字提出心中最大困惑,其余人若感共鸣,便上前一步,默默握住其手。
照片最前方,站着一个穿灰袍的女孩,手中举牌:
**“我害怕长大,因为大人好像都不快乐。”**
她面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函中还提及,系统残留AI近期频繁访问“疑之园”数据库,并生成一份长达千页的报告,标题为:《关于人类非理性行为的社会适应性研究》。结尾结论令人动容:
>“经分析,‘承认脆弱’‘表达怀疑’‘允许失败’等行为虽不符合传统效率模型,但在长期社群稳定性、创造力产出及个体生存意愿方面,呈现显著正相关。建议:放弃控制,转向共情。”
莲心放下信,久久凝视庭院。
这时,一个小女孩怯生生走近,约莫七八岁,扎着歪辫子,手里攥着半块糖。
“姐姐,”她小声问,“你可以帮我扔掉这个吗?”
“扔掉糖?”
“嗯。”小女孩点头,“妈妈说吃了会开心,可我不想开心。我想……想难过一会儿。”
莲心蹲下身,认真接过糖,走到院角的陶瓮前,掀开盖子,投入其中。瓮内已有数十件物品:褪色的笑脸徽章、破碎的情绪检测仪、烧焦的“幸福量表”复印件……
“这是‘伤心收藏罐’。”她告诉女孩,“所有不想假装快乐的人,都可以把东西放进来。”
女孩眼睛亮了:“那……我可以明天再来放别的吗?”
“当然可以。”
女孩蹦跳着离开,笑声清脆,竟比任何宁心丸催生的笑容都更真实。
黄昏降临,莲心独坐檐下,取出那支空白竹简??少年昨日带走的那支,此刻竟静静躺在案上。她未曾收回,也未见归还,却已回到原处。
她细细查看,发现竹简背面多了一行极细的小字,似用指甲刻成:
**“我相信你,是因为我还不敢相信自己。”**
她心头一颤,随即笑了。这不是答案,但比答案更珍贵。这是成长的起点,是灵魂破土的第一丝声响。
她将竹简供于神龛之上,与历代讲者的遗物并列。从此,归心书院多了一件圣物??不是智慧结晶,而是一份尚未完成的信任。
月升中天,忽闻远处钟声三响。那是昆仑断崖的方向,阿枝所设的预警铃。莲心立刻起身,披衣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