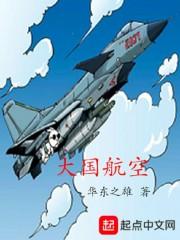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家父宋仁宗 > 第221章(第1页)
第221章(第1页)
得了孩童叫起,三位昨日与友人同好相谈至半夜的苏姓相公也揉着宿醉的脑袋起了。
正如孩童所期盼的那样,那位脸上带着笑的大苏哥哥又趁着他的父亲苏老爷不察,小小的招手将他叫至身前,塞了一块比前番还要大的炊饼给他。
至于那位小苏哥哥还是老样子,看到了但没有做声。不过这回似乎是熟悉了流程,并没有展现出惊讶来,反倒是小小挪了两步,为他与大苏哥哥之间的动作做着掩护。
苏洵如今已是年过不惑的人了,哪里会觉察不到两个儿子的小动作,但也权当不知。
原因有三。第一,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家他们寄宿的人家家境如何,他是亲眼所见的。两个儿子有仁善之心,也算不枉他一场教导。
其二,两个儿子情谊一如幼时,还学会了相互打配合瞒他这个老父亲,心中欣慰是要站了上风的。
至于其三嘛,寄宿民家不比客栈,能与人为善还是要尽量与人为善,不然难保被人敲闷棍。
再说这家人也是识得好的,这几日他们父子三人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带回来谈诗论赋,畅聊古今,常通宵达旦,这家人不仅没说什么,还从没断过热茶。
但华夏式父亲的通病便是心中的默许支持不妨碍口中找茬。
苏洵静静看着儿子们自以为得计地完成了馈赠,冷不丁转过身道:「吃饱了吗?」
苏轼苏辙都是被吓得身体一抖,到底是苏轼这个当哥哥的承担了更多,硬着头皮答道:「吃饱了。」
苏洵一边慢条斯理地擦着胡须上的食物残渣,一边说道:「今日要拜见横渠先生,汝等可做好准备了?」
横渠先生指的是张载,也是如今聚集在奉符县中最有名望的士子。
张载年少丧父,奉养寡母,拉扯幼弟,造就一派沉稳性格。
青年时又目睹夏人屡屡犯境,朝廷一败再败,不停退让,令喜谈兵的他很受刺激,年方弱冠便写出《边议九条》,上书当时主持西北军事的范仲淹,甚至打算组织民团去夺回洮西之地。
不过当范仲淹在读了他的文章,接见他之后,认为他可成大器,当在儒学上下功夫,将来教化万民,婉拒了他的弃笔从戎请求。
张载也听劝,归乡后刻苦读书,至如今已无论儒丶道丶佛,尽可信手拈来,一派大家气象。
听说此次太子前去探病范相,问天下有何在野遗才,范相头一个说的便是他。
所以太子特下教令命他至此,要择机召见他。
也正因有张载这尊大神镇在奉符县,怀揣着撞筹投稿与高官们混个眼熟的众多士子们才逐渐形成了讨论学术,切磋文章的氛围。
今日所谓的拜见,实际上是张载邀请他所看中的士子相互切磋辩驳,好助人扬名的。
可以预见的是,优胜者必然好处多多。哪怕此次科场失意,也能引起朝廷注意。
说到切磋辩驳,苏轼瞬间就来了精神,迫不及待说道:「唯程氏兄弟,章氏叔侄可稍为敌手,余者诚不足惧也。」
程氏兄弟指的是程颢丶程颐,这两人与苏轼苏辙一般,也是同胞兄弟。
至于章氏叔侄,指的则是章衡与章惇这对族叔侄。
程氏兄弟与张载有亲,张载曾对外言,论易学,他不如这两个晚辈,程氏兄弟因此声名鹊起。
也有人听了后不服上门找茬辩驳的,但无一例外折戟沉沙,有些人输了之后甚至直接要拜入两人门下。
至于章氏叔侄,乃是出自世代簪缨的蒲城章氏,两人尚且年少时就被任宰相的章得象以使族中子弟见青冥高天为由招到了东京城,稍长入国子监进学,如今已然是国子监头面人物。
而且尽管章得象已然过世,可他们的同族章楶可是以武立世,是太子殿下面前也说得上话的人物,所以也极受人追捧。
苏洵很欣赏大儿子的自信,十二岁即过了童子试的大儿子也的确有这个本钱。
但过分傲气是很容易吃亏的,尤其是蜀地士子向来为中原所轻。
所以他横了儿子一眼,带着警告道:「不可浪言。」
然后转向小儿子:「子由,你怎么看?」
苏辙也没有辜负他的名字,沉吟片刻后方道:「确乎不如二哥者众矣。」
但是赶在苏轼尾巴疯狂摇摆前又转向苏轼认真说道:「但二哥你需晓得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道理。
「咱们昨日不是还听说了吗,横渠先生见了太子殿下身边的曾学士,对曾学士的那位弟弟可是赞不绝口呢。」
苏轼口中应下,面上却是一派不以为然。
花花轿子人抬人,顺着杆夸人谁不会啊。
苏洵见了暗暗摇头,还是太年轻,欠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