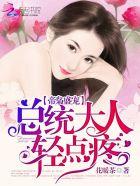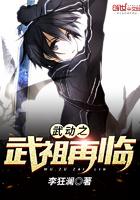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无极! > 第3章傲慢(第1页)
第3章傲慢(第1页)
‘倒与我所想一般无二。’
庄瑾微微颔首:‘京师永安的繁华,若想享受到,需要实力、背景为支撑,再或身体、尊严,以及能付出的一切交换,不然,就会是被充为螺丝钉,成为被享受的基数。’
‘所幸,这。。。
风起时,山外的云还未散。那页残稿在空中翻飞,像一只不肯落地的纸鸢,掠过屋檐、树梢、田埂,最终被一个放牛的孩子拾起。他不认识字,却觉得这纸上划出的痕迹好看,便夹进竹笛里,吹着走了。笛声呜咽,穿林渡谷,惊动了溪边浣衣的妇人,也惊醒了庙中打盹的老僧。
而此时,在东海之滨,一艘无名小舟正逆浪而行。船头站着一位老者,灰发披肩,手持一杆竹杖,杖头挂着半片烧焦的书页??正是《伪无极经》的残角。他不言不语,只盯着远方海平线,仿佛那里藏着某种回应。
三日后,南方传来消息:岭南某村塾夜间失火,火势不大,却将整整一墙典籍化为灰烬。但次日清晨,村民发现废墟之上立了一块新碑,上刻《自明章》全文,字迹刚劲如刀劈斧凿。更奇的是,碑文并非墨书,而是以疫区死者骨灰调漆写成,黑中泛白,触目惊心。
“这是谁干的?”官府震怒。
没人回答。
可接下来的日子,类似之事接连发生。西北驿站墙上浮现《问权篇》节选;北方雪域寺庙金顶下悬起真本《无极经》抄卷;就连皇宫围墙上,也有人用萤粉夜书:“权力须经万民审视。”天亮即消,夜里又现,如同魂魄不灭。
朝廷查无可查。禁军巡街百遍,只抓到几个孩童,手中攥着炭笔,嘴硬不说来源。审讯官喝问:“谁教你们写的?”
孩子仰头答:“我自己想的。”
“胡说!你才七岁!”
“可我识字了。”孩子认真道,“先生说,识了字,就能说出心里的话。”
此话传入宫中,皇帝沉默良久,命人将那孩子赦免,并赐纸笔一套。
与此同时,京畿之外悄然兴起一种新行当??“传音人”。他们不是信使,也不送文书,只是背着布袋,走乡串镇,在集市、茶楼、学堂门口高声诵读一段段文字。有人听罢流泪,有人怒斥荒谬,更多人默默记下,回家讲给孩子。
官府起初欲加禁止,却被御史台驳回:“若连声音都怕,何谈新政?”
于是这些“传音人”越走越远,甚至深入守序殿控制之地。他们在深夜敲响书院偏门,低声问:“要听真的吗?”接头者点头,便递上一枚铜牌,背面刻着五个小字:“你可以不一样。”
这铜牌原是传火会旧物,如今已遍布天下,连边关戍卒腰间都有悬挂。有人笑称:“如今最值钱的不是金锭,是能读真经的胆量。”
然而,暗流从未停歇。
某夜,西南群山深处一座废弃矿洞内,火光摇曳。十余名黑袍人围坐一圈,中央摆放着一本金丝装帧的《圣典》,翻开处赫然是篡改后的《无极经?顺命篇》。主座之人缓缓开口:“三年来,我们容忍混乱,是为了让‘自由’二字变得令人恐惧。当百姓发现所谓‘觉醒’带来的是争执、分裂、父子反目,他们自然会渴求秩序。”
左侧一人低声道:“可民间已有应对。那些‘巡理团’四处宣讲格物之法,连农妇都会算雨水周期,工匠也能制简易净水器……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重建规则。”
主座冷笑:“那就让他们建。等他们尝到治理之难,便会明白??没有权威的共识,终将归于chaos(混乱)。”
另一人犹豫片刻:“可顾怀瑾最近行为异常。他在柳巷放走萧林叶后,虽未受惩,却屡次拒绝参与新伪经修订。昨日竟提议设立‘对照版’,允许真伪并存……”
“他知道太多了。”主座冷冷道,“当年我们救他性命,便是看中他理性克制,能成为理想的工具。可惜……人心终究不可控。”
洞外忽有响动。一名侍卫跌撞而入:“大人!不好了!北境第三印刷坊被人突袭,所有库存伪书皆被泼墨,封面改题‘谎言录’三字!现场留有一柄木剑,与萧林叶所用极为相似!”
众人哗然。
主座却笑了:“木剑?那已是故人遗物。真正的武器,从来不在手上。”
他站起身,望向洞顶裂隙中透下的星光:“让他们以为胜利在握吧。真正的战场,不在街头巷尾,而在下一代的心中。”
数日后,京都国子监举行首次“思辨大考”。题目仅一道:“若《无极经》与皇帝诏令相悖,汝当如何?”
全场寂静。考生们握笔沉思,有人额头冒汗,有人嘴角微扬。最终答卷纷呈:有言“遵经反诏”,有谓“两全其美”,更有学生写道:“先问诏令为何而立,再察经义本意何在,最后询于百姓之心。”
此卷被陈砚秋亲点为魁首,张贴于观文阁外。围观者议论纷纷,一名老儒抚须叹息:“昔年科举只考忠顺,今竟容此悖论……世道变了。”
身旁青年接话:“不变的科举,才是祸根。”
此事震动朝野。李崇安闭门三日,复出时上奏请设“经义仲裁院”,由儒道释三家共议经典释义,以防“邪说横行”。皇帝批曰:“可设,但须加入民间学者五人,且议事过程公开。”
李崇安气得摔杯:“陛下这是要把圣贤之道变成市井争论!”
皇帝只回一句:“从前争论在暗处,如今摆在明面,已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