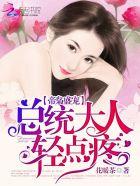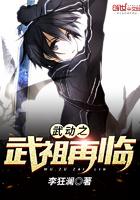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无极! > 第3章傲慢(第2页)
第3章傲慢(第2页)
就在各方角力之际,那位曾因防疫入狱的女医再度现身。她并未留在京城享荣华,反而带着几名弟子奔赴边陲,建立“格物堂”,专研疫病、水利、农耕。她提出“实证八法”:观、测、记、比、推、验、复、传。每一项皆要求数据详实、过程可查、结论开放质疑。
起初无人理会。直到某年大旱,官府依古法祈雨半月无效,而格物堂根据历年气象记录预测降雨节点,精准至日。百姓争相效仿,自行搭建简易测雨器。
从此,“信证据”渐渐取代“信祖训”。
但变革从不温情。
一年冬,北方某县爆发粮荒。县令按旧例开仓赈济,却发现粮库空虚。追查之下,竟是本地豪绅勾结官吏多年虚报储量,借新政之名骗取朝廷补贴。愤怒的饥民包围县衙,demands(要求)严惩。
县令欲安抚,引用《无极经》:“民为邦本。”
人群中有人大喊:“那你为何纵容贪官?”
另一人厉声反驳:“你懂什么!若现在闹事,明年就没钱修渠!”
争吵升级,几乎械斗。关键时刻,一名巡理团成员站上石台:“各位!我们学《无极经》,不是为了吵架,是为了找到更好的办法!”
他掏出一份手绘图表,展示历年税收与支出对比,又列出周边三县平均储备量,证明该县确实存在系统性贪腐。
“我们可以愤怒,但不能失控。”他说,“我们要的不是杀几个人泄愤,而是建立永不空仓的制度。”
人群渐渐安静。
事后,这份报告被送往京都,引发“透明粮政运动”。各地陆续推行“双账制”:官府一本,民间监督团另记一本,每月对账公示。若有差异,立即彻查。
有人讥讽:“这是防贼啊。”
回应者淡然:“若官如家人,何惧监督?”
然而,最深的裂痕出现在思想内部。
十年过去,《真本无极经》已成显学,但解读却千差万别。有人从中读出平等博爱,有人看出个人至上,更有极端者宣称:“既然人人可质问神明,那我也可自称神明!”
这类言论最初被视为荒诞,直至一名自称“新觉者”的男子聚集数千信徒,占据山头,宣布脱离王朝管辖,实行“绝对自由”。他们废除婚姻、私产、律法,声称“心灵纯净者无需约束”。
初期颇受追捧,尤以失意文人、流浪游士为多。可不过半年,内部陷入混乱:资源争夺、暴力频发、妇女被强迫“献身觉悟”。
消息传出,举国哗然。
朝廷欲派兵剿灭,却被皇帝制止:“他们是病症,不是敌人。若我们只懂镇压,说明我们仍未理解萧林叶的教诲。”
于是,一道奇特命令下达:派遣十位学者、五名医师、三位巡理团代表,进入该社群实地调查,并撰写《自由实验报告》。
三个月后,报告出炉,长达三百页。其中不仅记录乱象,更剖析根源:
>“自由若无责任支撑,便会堕落为任性;
怀疑若无求真引导,终将沦为怀疑一切;
解放若不伴随教育普及,只会让弱者更弱。”
末尾附言:
>“我们曾以为打破枷锁即是终点,如今才知,那不过是起点。真正的考验,是如何共同建造一座不会倒塌的房子。”
此报告刊行天下,引发空前讨论。连偏远山村的茶馆里,都能听见老人摇头感慨:“原来‘不一样’这三个字,背后要背这么多东西。”
也是这一年,海外共议会派使者来访。他们带来一本《世界宪章》,其中明确写着:“凡人类,无论出身、性别、肤色,皆享有追问真理、参与治理、追求幸福之权利。此精神源于东方《无极之道》。”
使者请求迎请萧林叶遗骨赴外海安葬,以示敬意。
朝廷婉拒:“先生骨血归于故土,但他思想早已四海为家。”
作为替代,双方约定每三年举办一次“无极论坛”,各国学者齐聚,共议文明前路。
而在这一切喧嚣之外,一个小女孩正坐在村口石墩上,捧着一本破旧课本。她手指笨拙地描摹着一行字:“你可以不一样。”
母亲走过来看见,皱眉:“这书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