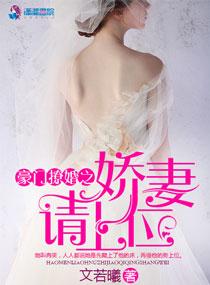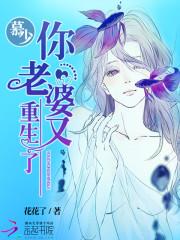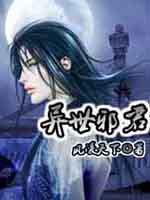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年代,二狗有个物品栏 > 第730章病房里的姑父(第2页)
第730章病房里的姑父(第2页)
那是谢兰花的声音。她还活着。她在等一个人,一个她以为早已死于战火的女孩。
“她记得我。”阿禾喃喃,“哪怕我不是她的亲孙女……她还记得。”
林知夏迅速调出历史档案:“1949年迁台名单显示,谢兰花确有一位双胞胎妹妹谢兰芳,登记年龄六岁。但在途中失散,记录标注为‘失踪’。”
“而我们的谢兰……”她顿了顿,声音发紧,“户籍资料显示,她是1950年冬天出现在知夏镇的,由一位路过的修女带来。当时她高烧昏迷,只攥着一本菜谱本。”
两人对视一眼,心跳如鼓。
真相缓缓浮现:那个在南京大屠杀中失踪的母亲,逃到了江南,生下双胞胎女儿。战乱中,她被迫将两个孩子分别托付给不同的人。一个随军去了台湾,一个流落浙南小镇。她们各自长大,各自嫁人,各自守着一首童谣,却不知道对方还活着。
七十年后,一首歌,把她们重新连在一起。
阿禾抓起背包,抱起布狗:“我要去马祖。”
“不行!”林知夏拦住她,“那边政治敏感,两岸关系紧张,你私自入境会被扣留!而且……特勤队已经在追查所有与‘静音事件’相关的人员。你一旦出境,很可能再也回不来!”
“可总得有人走完这条路。”阿禾平静地说,“谢兰把我养大,教会我用食物记住爱。如果我不去见她姐姐最后一面,才是真正的背叛。”
布狗跳上肩头,紫瞳闪烁:“我陪你。”
林知夏咬着嘴唇,良久,掏出一枚U盘塞进她手心:“这里面是所有‘回声通道’的密钥和备份数据。如果你失败了,至少还有人能继续。”
“不会的。”阿禾微笑,“我们会回来。因为春天还没讲完它的故事。”
三天后,一艘渔船悄然驶离浙江渔港。船老大是个沉默寡言的老渔民,听说是要送人去马祖寻亲,只问了一句:“是不是为了那首歌?”得到肯定答复后,他点点头,递上一件旧渔袍:“穿上吧,海警认不出你。”
海上风雨交加,雷达全盲。布狗趴在甲板上,紫芒顺着海浪扩散,形成一道隐形的护航屏障。每当巡逻艇靠近,仪器便会莫名失灵,仿佛被某种古老的力量驱离。
第五日凌晨,渔船靠岸。阿禾踏上马祖土地,湿冷的风吹乱了她的长发。远处山腰上,一座老旧的防空井静静矗立,藤蔓缠绕,如同沉睡的巨兽。
当地村民见到她,竟无一人惊讶。
“你是来听她唱歌的吧?”一位老太太拄着拐杖说,“每天夜里,井里都会传出童谣。我们都知道,她在等人。”
“你们不怕吗?”阿禾问,“官方不让提这些事。”
老人笑了:“怕?我们都老了。但孙子们会记住。只要他们还会唱,我们就没输。”
阿禾走向防空井。布狗跃下肩头,前爪轻触井壁。刹那间,紫光自裂缝中渗出,如同血脉复苏。
她蹲下身,对着井口,轻轻开口:
>“月儿弯弯照九州,
>几家欢乐几家愁……”
歌声未尽,井内已有回应。
>“几家高楼饮美酒,
>几人流落在街头……”
声音虚弱,却坚定。那是谢兰花,躺在病床上,由孙子架着手机连入紫蝶网络。
视频画面切入:一间简陋的病房,墙上贴满了手抄的菜谱,字迹与谢兰的一模一样。床头放着一双洗得发白的布鞋,针脚细密,正是知夏镇特有的绣法。
“姐姐……”阿禾哽咽,“我是小禾。谢兰……是我的奶奶。”
屏幕那头,老人浑浊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