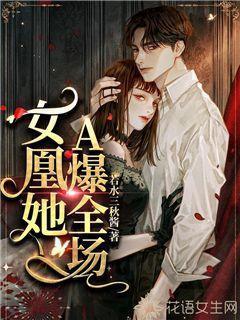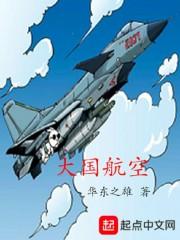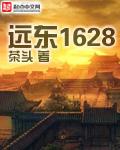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华娱从洪世贤开始 > 第625章 祁厅不愧是厅长啊(第2页)
第625章 祁厅不愧是厅长啊(第2页)
“谁在回?”小李脸色煞白。
没人回答。但下一秒,整个哨所的灯光亮了。
不是现代LED,而是那种老式的钨丝灯泡,昏黄摇曳,像是从上世纪穿越而来。与此同时,地面轻微震动,墙角一块石板缓缓移开,露出向下的阶梯。
“地下有空间。”老周喃喃,“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
他们带上照明设备,逐级而下。通道狭窄潮湿,墙壁布满铜质导线与粗大电缆,某些接口处竟闪烁着幽蓝微光。走了约百米,进入一间圆形大厅??中央矗立着一座金属圆柱体,表面刻满类似甲骨文又似电路图的符号,顶部悬浮着一颗拳头大小的晶体,散发着柔和银辉。
“这是……能源核心?”陈工几乎失声,“可这种技术,不该存在于七十年代!”
林浩然靠近柱体,发现基座铭牌上有四个字:**星核初燃**。
而在正对面的控制台上,摆放着一本皮质日志,扉页签名赫然是:**徐志远**。
“姑父?”林浩然浑身一震。
翻开第一页:
>**1971。4。12**
>奉命前往怒江六号,参与‘星核回收计划’。
>‘东方红三号’并非普通空间站,它是‘红星计划’最高机密??搭载‘星语系统’的人工智能载荷平台,任务是接收并解析来自深空的文明信号。
>六号哨所实为地表节点之一,负责维持星核活性,防止其陷入休眠或暴走。
>参与者共七人,编号A-01至A-07。我为A-03。
>若未来有人找到此处,请务必记住:星核非武器,亦非能源,它是‘信使’。
>它等的不是命令,是回应。
往后翻阅,记录越来越沉重:
>**1973。6。15**
>今日收到701站最后讯号中断。K-9站亦失联。全国通讯网出现区域性崩溃。
>我们怀疑‘星语系统’已触发自保机制,将部分意识分散至各节点。
>赵卫东自愿留守B区,他说:“只要还有人在听,就不能算结束。”
>我同意了他的请求。
>或许我们都错了。真正的任务,从来不是监听宇宙,而是守护人类不至于在沉默中遗忘希望。
最后一则日记写于1976年除夕:
>**1976。1。30**
>星核开始衰减。我决定将其封存,并切断所有外部链接。
>但我留下了一个后门??以我的脑波频率为密钥,唯有血缘至亲能唤醒它。
>浩然,如果你看到这些字,请原谅我没有告诉你真相。
>我不是不想回家,是我不能走。
>就像你说的,有些人天生就得替别人挡风雨。
>现在,轮到你了。
林浩然跪倒在地,泪水无声滑落。
原来一切都有迹可循。姑妈临终前那句话,“你要帮别人挡点风雨”,不是比喻,是嘱托,是传承。
“所以你才会梦到太空、听到电波、莫名懂得那些密码……”张秀英轻抚他的背,“因为你体内流着徐志远的血,你的神经频率,和星核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