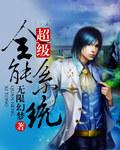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我的哥哥是高欢 > 第259章 隐形的助力(第1页)
第259章 隐形的助力(第1页)
高羽特意令人外出打探了一番。
祖?、宋游道二人在城中巡游的场景十分热闹,毕竟有玄甲军士卒亲自开道,又是敲锣打鼓的,这份殊荣其他人何曾享受到过?
千金买马骨。
高羽要的就是给于祖?、宋。。。
高欢的目光在高洋身上停留片刻,随即缓缓移开,落在殿中那七名新科进士身上。他负手而立,眉宇间沉郁如云,似有千钧压心。殿内寂静无声,连烛火都仿佛凝滞不动。良久,高欢才低声道:“你既愿入丞相府,便依你所请。”
此言一出,众人皆是一震。
司马子如眼中精光一闪,随即低头掩笑;崔暹则微微蹙眉,似有不解;杨?默然不语,目光却悄然扫过高洋,又落回高欢脸上。唯有玄甲军士依旧肃立如铁,纹丝不动。
高洋心头狂跳,面上却竭力维持镇定,深深一揖到底:“谢丞相成全,在下必当竭尽全力,不负所托。”
“莫要说得太早。”高欢声音冷峻,“我府中属官,非但需才学出众,更须品行端方、忠心可鉴。你既以科举入仕,便当知我设此制,为的是破除门第之弊,拔擢寒微,振兴国纲。若你只为攀附权势而来,不如趁早退去。”
高洋脊背一凉,连忙道:“丞相明鉴,在下绝无此心!只愿效犬马之劳,辅佐丞相,安邦定国。”
高欢未再言语,只是轻轻挥手。刘一得令,立即转身离去,不多时便领着状元与探花步入殿中。二人皆身着?衫,头戴乌纱,神情恭谨,步履沉稳。那状元姓李名元度,出自陇西寒门,文章锦绣,策论尤佳;探花名唤王允之,乃太原王氏旁支,虽非嫡系,亦具才名。
“尔等可知今日召见之意?”高欢开口问道。
李元度上前一步,朗声道:“回丞相,朝廷开科取士,意在广纳贤才,共图大业。我等蒙天恩眷顾,得登金榜,自当肝脑涂地,报效国家。”
王允之亦随之附和,言辞恳切。
高欢微微颔首,继而道:“然则,新朝未立,旧政犹存,八部空缺虽多,却不可轻授。尔等初入仕途,宜先入翰林院观政三年,待资历既深,再行擢用。”
二人闻言,面色微变,却不敢反驳,只得齐声应诺。
此时,高洋忽上前一步,拱手道:“丞相,学生斗胆进言??今国家草创,百废待兴,用人之际,何须拘泥于资历?若使真正英才埋没于翰林清谈之间,岂非可惜?”
殿中众人皆是一惊。
崔暹眉头一皱,正欲开口训斥,却被杨?轻轻按住手臂。司马子如则嘴角微扬,似笑非笑地看着高洋。
高欢目光如电,直射高洋:“你欲如何?”
高洋挺直身躯,毫不退缩:“学生以为,此七人皆才堪大任,尤以李元度、王允之为最。若能即刻分派要职,或入吏部理铨选,或赴户部掌财赋,或委以地方牧守之责,则新政可速行,民心可速安。况丞相府亦缺员甚多,不妨择其优者补入,一则可试其能,二则可察其心。”
一番话说罢,满殿俱静。
良久,高欢忽然笑了。
不是冷笑,也不是讥讽,而是一种罕见的、带着几分赞许意味的笑意。
“好一个‘试其能,察其心’。”他缓缓道,“你倒是有几分见识。”
高洋心中稍松,正欲再拜,却听高欢话锋一转:“然则,你可知为何我要设科举?为何要打破九品中正之制?”
高洋一怔,答道:“为的是使寒门子弟亦有机会出仕,不致令天下英才尽归豪门。”
“不错。”高欢点头,“但我更要立一个规矩??无论出身贵贱,皆须经磨砺、受考验,方可担重任。若今日因你一言,便破例擢升,那与昔日门阀私相授受有何区别?我又何以服众?”
高洋顿时语塞。
高欢盯着他看了许久,终是叹了口气:“你心思敏捷,志向不小,这很好。但为政之道,不在逞口舌之利,而在审时度势、步步为营。你既愿入我府中,我便给你一个机会??从记室参军做起,掌文书机要,每月呈递一份政议,若三年之内,能让我动容一次,我便亲自荐你入台阁。”
此言一出,殿中众人无不侧目。
记室参军虽为属官之职,地位不高,却是丞相近臣,常预机密。且“每月政议”之令,实为特例,非亲信不能享此殊遇。更关键的是,高欢亲口承诺“荐入台阁”,等于为其铺就了通往权力中枢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