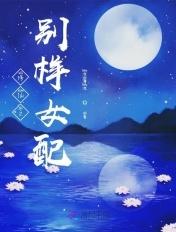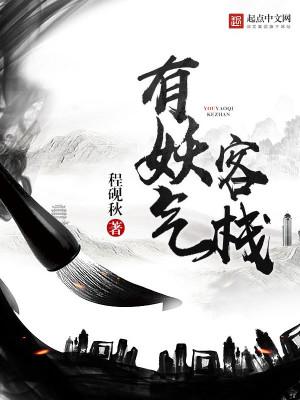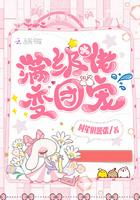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帝秦设计师 > 第95章 想吃画饼用我儒家(第3页)
第95章 想吃画饼用我儒家(第3页)
>
>今天,他们审判的不是某个人,
>而是我们共同的记忆。
>而我终于相信:
>若有一日黑暗重临,
>那些曾举灯走过废墟的孩子,
>必将再次点亮星河。”
文章发布后,全国多所学校将其编入新学期教材。有教师反馈,学生们自发组织“记忆守护小队”,定期检查本地政务公告的真实性,并向“心渊”系统报送可疑案例。
***
转眼夏至,万物繁盛。
在楼兰旧址,第二?少年议事庭如期召开。议题更加深远:
一、“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应强制标注‘非人类创作’标识”;
二、“国家是否有权在紧急状态下暂停部分认知自由”;
三、“逝者记忆数字化后,是否属于公共遗产”。
尤其第三项,引发空前讨论。
一名匈奴少年提出:“我祖父战死后,他的战斗记忆被制成纪念影像,在节日播放。可后来我发现,那段记忆被删减过??他其实曾反对战争,却被剪成了主战派。如果我们连死者的声音都能修改,那还有什么不可篡改?”
此言如雷贯耳。
经过七轮辩论,大会通过决议:所有数字化遗忆必须保留原始版本,存入“心渊?永夜区”,任何人调阅均需三人联签,并记录用途。同时设立“记忆祭日”,每年夏至,全国默哀一分钟,纪念所有被遗忘、被扭曲、被压制的真相。
仪式举行当日,咸阳宫前九柱齐鸣,醒世钟响十九次。
而在民间,一场静默的变革正在发生。
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在餐桌上实行“每日一问”:每个成员必须提出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无论大小。有孩子问:“为什么邻居爷爷总说秦人抢走水源?”家长便带他去查阅水利档案;有母亲问:“为什么村里女人不能继承田产?”全家便联名发起村级公议。
更令人欣喜的是,“萤石灯运动”已从城市蔓延至荒村野岭。偏远山区陆续建成三百余座微型真相站,配备太阳能供电的核查终端和语音交互系统,专为不识字者服务。一位盲人老者通过触觉屏幕听完政策解读后,含泪说道:“活了七十岁,头一回觉得自己听得懂话。”
王昭听说此事,特意命人将一台设备送至终南山认知修复中心,供康复者使用。他在附信中写道:
“知识不是特权,
而是每个人的呼吸权。
当你能听清这个世界的真实声音,
才算真正醒来。”
***
这一年秋,欧律狄刻再度来访。
她已卸去亲王之位,只为专心推动“跨国认知联盟”。在咸阳讲学三日,她站在杏坛旧址上,面对数千学子说道:
“你们改变了我对文明的理解。我以为进步在于科技飞跃,现在才明白,真正的跃迁,发生在一个人敢于对权威说‘我不信’的瞬间。”
她邀请王昭赴雅典参加首届“全球提问者峰会”,主题为“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守护思想自主”。
王昭婉拒,只回赠一幅画??仍是那个小女孩举灯发问的场景,背景却是世界各地的孩子,肤色各异,语言不同,却都高举着手,眼中闪烁同样的光芒。
他在画背面题字:
“灯不择地而生,